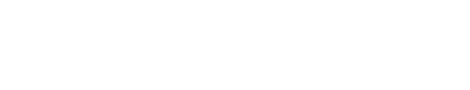范式转换生活中的例子(中国民族研究的困境及其范式转换)
今天的种族问题已经日益转变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在德国,英国乃至整个欧盟国家,新移民问题再次被纳入到民族问题的讨论中,并通过左翼和右翼政党政治得以体现。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许多事情和事件也不例外,但表达方式不同,问题的背景也不同;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正迫使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人种学家反思他们现有的研究范式是否处于危机之中,以及他们是否正面临着深刻的范式转变。
民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面对对当前在中国,的民族问题或现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存在着一种由不确定的知识和不可预测的现实变化所引起的困惑,产生了知识生产和实践的双重紧迫感。可以说,这种紧迫感与了解对民族问题的转化,密切相关。这种转化实质上改变了对民族问题的政治关注和民族研究的认识论取向。这里有五个需要明确提出的理解。它们从概念上澄清了目前对一些民族问题的研究趋势,使我们认识到这些偏差背后的认识论危机是什么。
首先,我们不能想当然地看待民族问题,解决转化提出的知识创造和积累的问题。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民族问题的知识是一种经验的积累,但很难形成对今后解决新问题的前提条件。从根本上讲,民族问题必须是一个实践问题,它取决于一种经验,但并不完全取决于这种经验。这是经验和实践之间的辩证张力,它依赖于启迪而不是因果关系。
其次,我们不应该把解决民族问题的智慧实践抽象地当作民族问题的理论建构,试图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从认识论上讲,这种方式几乎没有希望,这是一个浪费时间的文字游戏。历史表明,没有一种理论是万能的。此外,抽象理论越是宏大和精致,就越不能实际应用于解决实际的民族问题。相反,它们结合了现实情况的新概念和相应的策略,更有利于解决实际问题。
第三,我们不能忽视对国家背后现存权力关系的分析,而盲目地追随公民权利的世界性要求,并将其简化为国家自身的权利要求。除了对当前权力关系的分析之外,为了寻求更接近当地实践的权利和利益的定义和保护,这显然是对对国际主义概念或欧美化的人权实践的极其简单化的模仿。事实上,在少数民族的概念不断转化为权利和利益的同时,其寻求发展和变化的积极性却在逐渐降低,最终无法真正把握社会和文化的趋势。
第四,我们不能把原本属于文化层面的价值和价值问题看作是转化社会治理或制度的预定设计。这种做法显然不是从人民的标准来看待人民,因此也就不可能从民族的个人标准来看待民族本身,也就是说,不可能从人民的心态来安抚对民族的心,因此,既定的规则是徒劳的。与对,相比,文化或价值观的问题是虚幻的,不容易被人们抓住;就社会而言,尽管存在各种制度,但似乎有一个可以把握的现实,但背后仍有某种文化价值,社会最终仍在这种文化价值下运行。
第五,我们不能解决转化是一个单一的土著或原住民的问题。结果只能是,通过一个人为的定义,某个人群被束缚在某个保留地,这使得他们缺乏适应社会变化的创造力,最终只能听其自然。显然,在这一点上,没有人可以是一个天生具有土著特征的民族,而只是在多次迁徙中不经意地落入这个民族的构成之中;此外,国家和居住地的匹配是现代世界的产物,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只有在今天才有存在的价值。在其他时候,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实践的紧迫性和危机
就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而言,它真正呈现的或研究者所遇到的是一种紧迫感,这种紧迫感在问题意识和行动实践中都得到了强调。换句话说,面对对民族问题的新知识、新内涵、新语境和新形势,一种紧迫感在不同层面的社会研究实践中弥漫开来。这种紧迫感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体现在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两种危机:一是学术表达的危机,二是政治合法性的危机。
就前者而言,危机更多地出现在学术界的范围之内,由此引发的混乱突出地表现在对对现有学术研究规范的一般意义上的抵制或否定,而这种被抵制和否定的学术规范的基础显然来自于特定时期的西方社会科学的现有传统,尽管这一传统在西方后现代解构主义浪潮中也遭到了批判和抛弃。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这种抵制和否定的趋势逐渐被每个人感受到,正是因为他们各自领域中概念和话语表达的危机。
后一种危机与全球政治合法性危机密切相关,后者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密切相关。它不仅带来了社会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也导致了底层人民生活原有的自组织功能的丧失。传统的生活方式及其隐含的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各地消失,每个人都无缘无故地卷入了全球市场竞争。一旦中间的链条断裂,社会底层的人们仍将遭受第一次伤害,——。基于发展和进步理念的社会工程剥夺了他们原有的土地或其他基本生活资本,他们的日常生活完全或大部分依赖于外部世界市场的变化,他们的适应能力急剧下降。(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