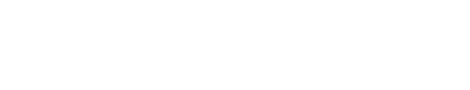语用学中的语境论(论翻译中的语境篡谋)
对话语活动赖以发生的社会情境的主观建构存在于认知心理系统中,是情境和言语之间的中介。只有考察具体语境,从源头上追溯“忠实”的框架和局限,摒弃传统翻译研究的二元论,以动态的、多元的模式研究语境与翻译的关系,才能避免西方中国和弗斯在理论研究上的尴尬,打开翻译研究的新局一面。在研究翻译时,我们不能把抽象的“忠实”视为理所当然,而只能停留在文本内部的语言转换来研究翻译的本质。
关键词:话语交际;翻译理论;忠诚;背景;篡夺阴谋
1.翻译的语境盗用
(一)篡夺语境
在显性和隐性代词指代、省略结构、无标记重复词汇(结构)和关系连词的形式上也存在差异。对等单位在翻译中的“自然”适应通常被理解为中性和透明的,但其根本原因是翻译文本中的“自然”和对原文中的“自然”的侵蚀。似乎一旦内容和形式在对,确立,翻译将不可避免地依赖和偏爱前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形式的牺牲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可以说,翻译的一个可能条件取决于对对形式的某种篡改和抛弃。
互文性概念可以解释译语语对对话语的篡夺。当一个符号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是进入时,两个文本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互文性”。(莱姆克,1985)赛博克(1986)将构成互文性的要素分为七种类型:指称(指另一个文本标题,指出一章中的出处),公式化语言,文学典故,自我引用,习语(经常使用但来源不明的思想和观点),谚语和格言,以及对在文本中的第一次经历的表达。莱姆克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互文性也存在于特定文本和它所属的文本系统之间。同类型文本群的互文性包括四个相似之处,即风格、主题、结构和功能。“互文性”强调某些文本要素能够触发文本前文本之外的知识和价值体系,这是一种贯穿内涵的参照机制,而不仅仅是一种主观联想。在处理互文性元素时,我们必须注意它们的信息状态(场、模式、基调、时间、地点等)。)在进入文本之后,他们作为话语行为的指称意图,以及他们与其他符号相互作用的符号功能。除了考虑源语本身的互文关系外,译者还应该考虑其在进入-译语体系下的互文性运作。有时,译者会遇到非常尴尬的情况,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严格的直译可能会增加读者的负担,而原文的文本特征可能会随着通常的补偿手段如注释和扩展而改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纳博科夫对普希金作品《奥涅金》的翻译。他的译文所附的注释远远超出了原文本身,因此,他的译文更像是一部解释性的学术著作。另一方面,如果过分强调译语体系的互文性,并在原著中加入读者熟悉的形式,异域文化色彩很可能会消失。早期,西方小说被章回结构所覆盖,而拜伦《哀希腊》被梁启超,马君武,舒曼苏、胡适的元曲、七言古诗、五言古诗、离骚体所覆盖,他们运用中国,独特的风格和结构,强行建立起译作与本土文学的互文性。这样,接受语境完全改变了原文,语言之间的差异被抹去,译语征服并编辑了原文。这可能只是一个极端的情况。在实际翻译中,互文性机制不会采用纯粹的异化或归化,而是两种方法的结合。翻译总是一种“杂合体”,既不是原生的外国文学,也不是原创的本土文学。在强调多元化的今天,人们可能更喜欢直译,要求翻译尽可能忠实地保持自己的特色。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译语的允许和接受是源语言在移植后获得新生的条件。
(二)情境情境的篡夺
首先,必须首先介绍和导入文本。翻译赞助商、出版社或其他机构根据特定标准确定哪些文本可以翻译,哪些文本值得翻译,并附上要求。译者本人也可以充当发起者。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消费主义日益盛行的今天,文化商业化和商品文化化已经侵蚀了传统文化和商品的区别,而利益驱动的对翻译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经典和严肃作品在翻译领域的衰落,以及畅销书、电影和电视剧的激增,表明市场已经成为指导翻译的无形巨人。
其次,读者和使用翻译的目的对对的翻译也有重要影响。读者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明显时代特征和特定文化背景的实体。由于行业、教育、社会经验、文化心理、观念和阅读取向的不同,对信息的价值和关键要求也不同。读者的期待构成了话语的无形牵引。忽视读者的现实和欲望,作品很难进入进入读者的视野,更谈不上生存和延续。
第三,由于文化之间的距离,原作者进入翻译后的命运取决于译语文化的态度。乔治菲茨杰拉德是19世纪英国的一名翻译家,他认为译者没有必要屈从于原作者。原著只为他提供了在译语运作的可能性。今天,一切都以原著为中心,翻译应该服从原著,反之亦然。一切都以译语,为中心,原著必须被译语,改写和操纵,这仍然是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第四,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翻译本身在文化中的地位也影响着翻译。在多元文化的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并不总是从属于原创文学。当本土文学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体系还不完整时(例如,在建国初期),或者对还处于其他文学体系的边缘,当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时(如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文学),或者正经历一个危机转折点时(如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文学和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翻译文学将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主要致力于引进外国作品来改变变现,创造一个文化新局来摆脱困境。因此,翻译要贴近原文,尽量复制和保留其形式要素和语篇关系。在其他情况下,翻译处于次要地位,主要目的是介绍和吸收他人的新思想。因此,翻译将更多地依赖于自身现有的模式和审美规范。
第五,译者无疑是翻译的核心和关键。根据他对对上诉因素的综合考虑,他进行了调解,并最终决定操纵原文的程度和方式,而不是原作者的“恰当、合理和正确”的言论。译者不可能像一些翻译理论家所要求的那样隐形和透明,他们将永远在翻译中铭记自己。
文化语境主要是指构成人们心理空间的思想体系或精神氛围,如文化传统、价值观、知识信仰、风俗习惯、历史事件、行为规范等。它在话语交际中起着宏观导向的作用。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宗教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李运兴,2000: 122)在不同时期人们对对“翻译伦理”的理解和表达中,文化阴谋十分明显。张培基、喻云根在1980年发表、2000年再版的《英汉翻译教程》一文中强调,译者的首要素养是“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较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水平,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深刻理解原著内容。”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导致译者理解和分析的差异,所采用的方法必然会影响原作的实现。翻译史表明,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可能需要极端的方法来操纵原作。20世纪50年代,中国一本流行的翻译教科书在谈到翻译时强调“忠实”是翻译的首要标准,但这似乎与另一个标准相矛盾,即翻译活动必须符合译语文化的要求。
二、结论
在研究翻译时,我们不能把抽象的“忠实”视为理所当然,而只能停留在文本内部的语言转换来研究翻译的本质。我们必须回到翻译活动的具体语境,从源头上追溯实现“忠实”的基本条件。如果我们摒弃传统的二元结构,采用动态的、多元的模式来研究语境与翻译的关系,就可以避免西方中国和弗斯在理论研究上的尴尬,打开翻译研究的新局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