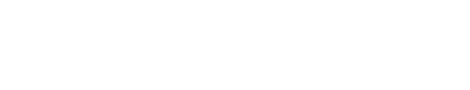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什么意思(被颠倒的历史的再颠倒)
2015年是延安文学运动发起80周年。一些长期在延安从事文艺研究的学者与湖南文艺出版社联手推出《延安文艺大系》。《延安文艺系》主编、原《求是》杂志副主编刘润为,先生,对该书的出版意义、革命文艺的产生和发展、对在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中的借鉴作用的基本性质作了全面论述。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自然应该成为文艺的主人。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人民文艺运动,开辟了民族冷战时期丰富多彩的文艺胜地。
问:刘,先生,今年是延安文学运动发起80周年。我听说你编辑了一本书《延安文艺大系》。你能告诉我出版这本书的意义吗?答:首先要说明的是,这本书的主要工作是由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同志完成的,特别是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的负责编辑徐应才一同志和其他同志只是做了一些服务工作。事实上,安排我当主编有点贪心,但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同志坚持要这样做,他们也没办法。说到这本书的意义,我认为它不仅是一部特定时期的文艺史料汇编,也是时代精神的载体;它不仅是荣耀和骄傲的纪念碑,也是人们获得智慧和勇气的启示录。它所包含的所有伟大意义将在创造新历史的伟大过程中以一种迷人的方式实现。
问:这有点太笼统了。你能扩展它吗?答:我们应该从人民的文学艺术权利入手。众所周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正如达尔文发现了有机世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也发现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规律,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它始终被纷繁多样的意识形态所掩盖:人们必须先吃、先喝、先住、先穿,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正是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生产了这些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没有人民的辛勤劳动,任何文学艺术的出现和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在从事劳动生产的同时,创造了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和半成品。例如,著名的《弹歌》:“破竹、续竹、飞土、追肉”是古代劳动者的绝唱;经典诗篇《木兰辞》的出版离不开文人的加工,但至少70%的功劳应归于人们的原创。纵观整个文艺活动体系,我们可以清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是文艺的第一创造者。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自然应该成为文艺的主人。然而,在剥削阶级统治的旧中国,基本的文艺资源被少数富人和贵族占据,人民不仅被剥夺了表达文艺的权利,而且被剥夺了享受文艺的权利。这无疑是对历史的逆转。
由于这种逆转,对自古以来从未停止质疑、不公平甚至不同程度的争斗。例如,白居易曾主张以人民的苦难作为对的形象(“唯唱使人生病”),并尽力推广他的诗歌;刘,玉溪甚至接触到了劳动所造成的艺术的社会现实(侯王印,一件美丽的珠宝,来自沙子的底部);郑板桥公开表示:“我画兰花、竹子和石头,是为了安慰在世界上工作的人,而不是为了享受世界的人。”然而,这些古代士大夫并没有说他们已经把立足点移到了人民一边,而只是说对人民在他们不公平的处境中有一些同情或人道的感情。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继承了梁启超的“三大革命”,高举“文学革命”的旗帜,号召“打倒贵族文学,建设轻松抒情的民族文学”,为动摇文艺领域的封建贵族作出了根本性的贡献,但这里所指的人主要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尤其是他们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是觉醒的劳动人民自己和觉醒的劳动人民的代表真正把劳动人民置于文学英雄的地位。问:你能谈谈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对的探索吗
甲:好的。应该说,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它就开始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紧密团结左翼文艺阵营,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文艺理论努力解决中国的文艺问题。从理论上讲,李大钊早在1923年1月就指出:“无论是文学、歌剧、诗歌还是口号,如果不以民粹主义的旗帜为指导,就决不能在当今社会传播,决不能赢得群众的赞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卷,第245页,第103010、《平民主义》页)显然,李大钊所提倡的是劳动群众的平民文学,而不是五四时期城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一般知识分子的文学。此后,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人通过《李大钊文集》提出:“新诗人必须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主张用文艺来唤起工农的阶级意识和革命勇气,并强调“尚未进入煤矿的作家”是“作家的耻辱”。在1928年开始的革命文学论争中,郭沫若主张文艺青年“去当兵、去民间、去工厂、去革命的漩涡”。程号召“把农民和工人当作我们的大象”。建国后左联,在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瞿秋白主张革命文艺工作者要“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培养群众的新习惯”,“表现革命的英雄,特别是群众的英雄”。在中央领导的苏区教育和文艺工作中,瞿秋白告诫革命文艺工作者不要闭门造车,要向高尔基,学习,去生活,去斗争最激烈的地方,接触群众,创造群众容易理解和理解的艺术。(见李伯钊1950年6月18日《中国青年》、《回忆瞿秋白同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领袖鲁迅,首先提出了文艺工作者改造自己世界观的问题。他说:“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作者是一个‘革命家’……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正是出于这种自我意识,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灵魂中的毒气和鬼气”,于是他“每个月和每天都与自己战斗”,“从其他国家偷火”(通过翻译马克思的作品),并且“自己做肉”。
从创作角度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统区革命文艺工作者顽强地推动了革命文艺运动,创造了一些具有历史主动性的工农形象。例如,田汉在1925年创作的以“五卅运动”为主题的话剧《人民日报》,热情歌颂了中国工人阶级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不屈精神。蒋光慈193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顾正红之死》(原名《田野的风》)以大革命前后农村复杂的社会现实为背景,反映了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摆脱反革命封建势力的束缚,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其中,对对贫苦农民王荣发在革命道路上的心路历程的描写,尤其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和生活逻辑,显示出巨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历史内涵。叶紫短篇小说集《咆哮了的土地》以他的家乡洞庭湖,为中心,描写了旧中国农村的深重苦难和蕴藏在广大农民心中的火山般的革命力量,揭示了人民革命最终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被鲁迅誉为回应压迫者的战斗文学。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人民文艺运动,开辟了民族冷战时期丰富多彩的文艺胜地。戏剧是苏联文学艺术中最生动的花朵。各种剧团、戏剧俱乐部和俱乐部遍布军队和城乡。例如,在毛泽东,调查的长冈乡, 兴国县,成立了四个俱乐部,每个村庄一个,每个俱乐部都有新剧。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剧作家们编演了《丰收》、《父与子》、《破牢》、《松鼠》等。反映革命斗争生活,深受军民欢迎,与国统区左翼戏剧运动形成了相互呼应。人们创作的民歌相互对立。唱民歌是苏联人民的悠久传统。自从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以来,民歌的风格发生了变化,成为人们表达新的感情、愿望和激情的有效形式。“民歌不浪漫,共产主义也不自由。当你开始共产主义郎,首先去唱民歌女孩带头。”受这些歌曲的启发,兴国县曾在三天之内组建了三支红军队伍,即劳模队、工人队和青年队,从而留下了“一曲三师”的千古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