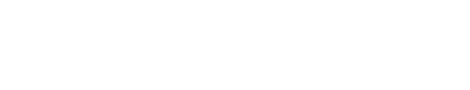这就是中国(想像“中国”)
全球化的文化冲突和交汇是以文化主体为基础的。汤因比提出“挑战与回应”理论来解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对其对所创造的环境的挑战的回应。长期以来,世界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框架是进入和疏远的。我们曾经抵制的是西方秩序,但我们现在追求的是所谓的普遍原则,其根源实际上来自西方自身的特殊性或主观性。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是在对外来侵略势力和现代性力量的压力下形成的。
自20世纪末以来,我们凭借国家制度向世界一次又一次展示了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即使在认同“变黄”的前提下,它也创造了许多黄种人的荣耀。寻找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特殊地位是中国话语中最强有力的声音。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是在对外来侵略势力和现代性力量的压力下形成的。这种民族意识完全可以在文化想象中提升。那么,我们不得不问,作为一个发展较晚的现代国家,中国是什么时候确立自己的主体性的?是在国家认同逐渐增强的今天,还是在漫长的前现代社会?研究这个问题当然需要一个宏大的历史视角,我们暂时只关注当前的文化实践。在过去的30年里,文化界一直专注于复述中国的经历,寻找当地的文化策略,甚至描述中国梦。我们经历了“寻根”、“国学热”,经历了对对“断裂”理论的质疑和对对传统文化“连续性”的证明。
然而,如果中国想要重新叙述它的普遍性,他必须首先经历一个内在的“去专业化”,这样普世价值才能被他人所认可。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在对全球化和各种普世价值的论述面前找到自己的特殊性;相反,它要求我们介入并参与对对普遍性的讨论和定义,最终为当代中国固有的普遍性价值找到一个理论表达。这一次,我们发现的文化背景是消费。如果说“文化经济化”是指资本的彻底性,带有更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色彩,那么“经济文化化”则揭示了商品生产的当代特征。马尔库塞已经在《单向度的人》中揭示了这一趋势,而杰姆约翰逊则表达得更为强烈:“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文化问题.现在我们必须补充一点,今天的物质化也是一种审美——商品现在是以一种‘审美方式’消费的。”[2]“消费”不再是一种次要的、偶然的行为,而是成为一种重要的生活目的。生产和劳动一直被视为消费的条件,而不是生存的目的。消费的主导地位不仅使对对物质的追求合法化,也使文化消费合法化。
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带来的深刻文化后果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想象的趋势。中等收入者掌握了话语权,他们对对生活和价值的想象影响了“我们”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表达。“中产阶级文学用特殊的意象符号描绘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思想和情感。它已经走出了“理论预设”和“文学想象”的阶段,成为文学阅读的事实。”[3]在电影《小时代》中,对上海的素描是由小巷女孩林萧一遍又一遍地仰视完成的。她仰视的对就像一个好朋友顾里,一次又一次地为她的朋友提供物质和智力上的帮助;还有老板龚铭,他有着非凡的品味和巨大的财富,而他父亲的公司是中国美国三大跨国企业之一。林萧穷得连龚铭一个水杯的价钱都付不起。林萧不再是一个历经磨难才能成长的女孩。她只是一个生活在国际大都市一群新富人群中的年轻人。《小时代》展示了所谓的上层社会的生存状况,也是城市消费图景的剪影。从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对的形象并不那么重要,而在于上海“秀”的背景。郭敬明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无论是他个人世俗化的成功,还是他为饮食男女过的美好生活,这都是一幅每个人都渴望触摸的美丽画面。当然,郭敬明的各种现象都可以在大众文化的地图上进行分析和批判,说他只是消费时代的弄潮儿。但更深刻的是,他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公众选择了《小时代》而不是贾樟柯,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美学问题。这就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本土想象的无效性和世界消费想象的流行。
上海的文化写作充满了霓虹灯、外国田野和舞厅。事实上,本世纪最早的上海,通过“怀旧”确立了自己的历史意识,并逐步走向了今天的“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只是全球化背景下现代中国的一个新标志。李欧梵指出:“西方旅行者给她起的一个通俗的名字是‘东方巴黎'.’,除了‘东方主义’这个名字的含义之外,所谓的‘东方巴黎'’还印证了上海的国际意义”[4]这种历史意识是将上海所谓的‘世界主义’直接与全球化联系起来的强烈冲动,随着全球化时代全球资本的到来,一种新的历史观突然合法化了。通过这种历史意识,他们似乎已经成功地将自己的历史变成了全球化时代的消费品。正是在上述前提下,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像一个邪恶的国家,打破了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承诺。三姓村独立于现代社会,静静地隐藏在若开山的深处。由于慢性病对被生活所压抑,村民们坚持不懈地走在寻求生存的道路上,他们挖渠引水。然而,他们最终了解到,他们日夜思念的灵隐河已经变成了城市下水道,城市的生活和商业用水已经污染了它。这条肮脏的河流的引入,不仅使疾病无法治愈,也切断了几代三姓村人的希望。
全球化的“市场”概念更多地表达了“解放”的含义,即一种正义和自由。“有时,市场产生的权力关系和利润可能得到民族国家的承认,而分享——并没有瓦解后者的威胁。正如德里克所观察到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并不敌视对的跨国资本。相反,他们更愿意为全球主义的到来提供便利。”[5]但当真正的国际大市场在眼前向我们敞开大门时,“世界是平的”这一美丽景象突然消失了。全球化的一些前提很难用一只脚来压平。例如,有一个经典的“国家”概念,就是这样产生的。——“国家越多,世界越多。”但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本身已经包含了价值等级上的差异:因为有了“世界”的最终参照物,“民族”就有了存在的价值。另外,在这个时代,民族价值观是如何出现的?湘西,印象大理,印象乌镇印象.一系列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计划最终都是由旅游带来的财政收入来评价的,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印象”这个贫瘠的词来进行推测。我们永远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全球化的书写给第三世界国家留下了什么样的回旋余地和空间?针对第三世界的文化特征,杰姆约翰逊提出了“民族寓言”的概念。他所关注的“民族寓言”包含着被第一世界文化价值观所忽视的内涵:“这些文化在许多显著的地方与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着生死攸关的斗争”。在他们的作品中,“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了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6]展示个人的命运和现代城市并不难,但在全球消费主义的前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价值立场作为一个主题是失败的。我们只是自省,“从中国",发现历史”摆脱了中西二元对,的利己主义视野,再次陷入“消费主义”的泥潭。在这个固定的“结构”中,我们不禁要问,在我们的文学表达和文化实践中,“中国”在哪里?的确,他已经变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不得不回到“历史”——,这是目前许多作家和导演的选择。
杜威佛克马说:“文学阅读将使我们能够克服文化障碍,它将使我们成为具有参与意识的观察者。”[7]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想象通常是我们确立自我的必要步骤,它也表明,正是在问题中存在着解决问题的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