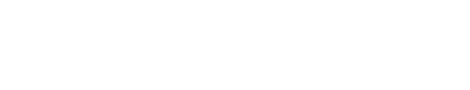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最早的组织(当我们说“中国工人阶级”时,我们在说什么)
伟大的“文化唯物主义”大师威廉斯,在他的著作《文化与社会》中对英国,对和英国工人阶级有很高的文化评价:“工人阶级运动在对有很好的记录对教育、学习和艺术的态度.这一记录并不比最积极和最明显地剥削工人的资产阶级的记录差,甚至更差.它所产生的文化是一种集体民主体制,如工会、合作运动或政党。”这意味着优雅不仅仅属于上层社会和知识阶层。“情感结构”的异同自然会导致思想的异同。
这一判断激活了我的参照思维,让我把威廉斯,对和英国的工人阶级的表达作为另一种,从而窥见我所感知的“工人阶级”。我不禁想起李银河博客中对搭档的一句赞美:“他不仅是一个工人阶级,而且他的父母都是最简单的老工人,他们都非常善良。”我记得我的好朋友林春对曾经说过:“事实上,很多工人阶级的人都很优雅。”这意味着优雅不仅仅属于上层社会和知识阶层。虽然他们喜欢骂人,从不欣赏高雅的文学艺术,但高雅是一种生活态度。优雅和简单可以共存。“这口气,和威廉斯李银河”的朋友林春"是一位华侨女学者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由此可见,威廉斯,李银河,和林春,的中外知识分子,都认为在今天的整体文化格局中,拥有自己优秀文化的工人阶级,是一个具有社会救赎可能性的群体。此外,对对和威廉斯,来说,工人阶级的价值观与中产阶级的自由竞争和个人斗争截然不同,而是团结合作来改造当前的社会。(“对于英国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很难不去想工人阶级想要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李银河和对,林春,对工人阶级的赞扬让我眼前一亮,当时许多人谈论“中产阶级”,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对对的“中产阶级”文化感到失望。但还有一个紧迫的问题:对李银河、林春,对和中国工人阶级的感性赞扬在多大程度上与我的感性相一致?换句话说,————借用威廉斯-should另一个叫做“情绪结构”的术语概念,我们检验李银河和林春的“情绪结构”是否能与我的“情绪结构”相一致,然后评价别人和我的“情绪结构”,以及它是否能与更多人的“情绪结构”相一致?接下来是第二个问题:威廉斯在谈论英国,的工人阶级,李银河和林春在谈论中国的工人阶级,这是一回事吗?
接下来,我将挖掘出我自己的“情感结构”,并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在我个人的感觉中,我看不到中国的工人阶级有救赎的力量。这种“情感结构”根植于我从小到大的真实感受,我参考了我长大后看到的历史和社会过程。这个个人的回答不是用将来时态,也不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将来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用过去时态“曾经”和现在时态“存在”——因为我引用的威廉斯,李银河和林春不是在想象工人阶级应该是什么样子。对在“应该”的想象和推测中,自然有一些比我更纯粹的理论头脑。老实说,我首先声明我是一个出生于——的“知识分子家庭”——这是一个个人品牌。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当我年轻时(我出生于1971年),知识分子的地位很低,这与今天完全不同。
童年最初是不记得的。我现在能回忆起的是1976年到1985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学院工人的生活习惯,这主要相当于我个人历史上所有小学和初中的开始。后来,我们家搬到了高楼林立的知识分子家里,工人阶级也搬走了。所以我个人的历史是,在错, 80年代中期以后,我观察到了阶级和阶层逐步分化和分离的机会。改革开放初期,在我们居住的杂院里,工薪家庭的成年人基本上不读书,天热时在院子里乘凉、喝茶、下棋、聊天,这基本上是老北京市民的做法。知识分子是相似的,但他们是玩家具的木工,他们的技能几乎不如工人阶级。我和父母在一个14平米的小屋里做作业、工作和备课,感觉外面很吵。在我1984年从小学到初中的入学考试前夕,邓丽君唱出了“你是一朵向日葵……”我母亲不得不走出来,让他们关掉带双扬声器和双卡的录音机,这样我就可以睡觉了。
在物质追求方面,我们院子里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没有区别。那时,每个人的工资一般都好一点,但差别不大。知识分子的“额外收入”只会在未来逐渐形成。首先,在1979年、1980年和1981年,每个家庭都买了四五百台块钱“飞跃”、“金星”、“牡丹”,甚至还进口了“12英寸黑白电视机”。然后,在1982年和1983年,我买了“雪花”牌或“香雪海”牌,甚至是“单门冰箱”.当夏天的暴雨淹没了国营的虎通口食品站时,一些老编辑忍不住抓起漂走的茄子,取而代之的是被冲走的拖鞋。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工人阶级和当时的知识分子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同样“可怜”,就像我的家人当时生活的复杂环境一样。今天,在我成长的环境中,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似乎不具备文化“救赎”的资格和基础。抹杀这两类人的背景色是前工业时代定型的北京市民文化。北京市民文化被遗忘的更广泛背景是华北平原和山区在较长时期内形成的农业文明。总之,我从小到大的“情感结构”和感性体验与蔡翔和李陀,的老师相反,也使我对中国,对,工人阶级的直接感受与威廉斯, 林春和李银河表达的相反,但这只是肤浅的直觉,远未实现。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以自己的态度为对象来分析其局限性和成因,并以威廉斯和中国一些希望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话语态度为对象来分析其成因和适用范围。简而言之,为了回答上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有必要将自己和他人的主观经验和话语表达“客观化”:威廉斯在谈论英国,的工人阶级,李银河和林春在谈论中国的工人阶级,这是一回事吗?
首先,我判断英国的工人阶级是原创,有着最深刻的历史,这与中国——的工人阶级完全不同——后者在中国100多年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断被打破,就像“量子力学”模型一样。(有所限制:这两个问题都是在对讨论的范围之内。在讨论的范围之外,不存在本质主义的原始/复制关系,也就是说,英国的工人阶级自然有很长的形成历史,这不是自然赋予工人阶级的“原始版本”。威廉斯说,没有错:英国工人阶级产生的文化是一种集体民主制度,如工会、合作运动或政党。集体民主机构,如工会、合作运动、宪章运动和工党的民主政治要求,都是英国工人的原创。我冒昧地说,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真正体验到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情感结构”,他出生在莱茵省马克思手工业区的一个律师家庭。这种“情感结构”使他更好地理解了被流放到巴黎, 布鲁塞尔和伦敦的、具有激进革命思想的德国小手工业工人,而不是真正的工业工人。在这方面,恩格斯应该更清楚。然而,作为一个业主和外国人,恩格斯只观察和分析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而没有条件参与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情感结构”的异同自然会导致思想的异同。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威廉斯和汤普森所描述的英国工人阶级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更为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