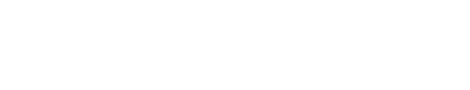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红字》中外在空间叙述的意识形态化研究)
《红字》第一章对“监狱之门”的描述如下:根据这一约定,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估计出波士顿的祖先在康海尔:附近修建第一座监狱的时间。这与艾萨克约翰逊境内一块土地被指定为第一座墓地的时间大致相似。在这个城镇建立了十五到二十年后,木制监狱由于风和太阳已经暴露了各种各样的旧痕迹,给这个狰狞阴沉的大门增添了一种悲凉的景象。像所有与罪有关的事情一样,监狱似乎永远不会年轻。
《红字》第一章对“监狱之门”的描述如下:根据这一约定,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估计出波士顿的祖先在康海尔:附近修建第一座监狱的时间。这与艾萨克约翰逊境内一块土地被指定为第一座墓地的时间大致相似。后来,以约翰逊墓为核心,围绕着它修建了许多坟墓,这些坟墓扩展成了英王礼拜堂的旧墓地。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个城镇建立了十五到二十年后,木制监狱由于风和太阳已经暴露了各种各样的旧痕迹,给这个狰狞阴沉的大门增添了一种悲凉的景象。栎木大门上沉重的铁器生锈了,看起来像是新大陆最古老的古董。像所有与罪有关的事情一样,监狱似乎永远不会年轻。在这座丑陋的建筑前,从房子的外墙到布满车辙的街道,有一片草地,上面长满了丑陋的杂草,如牛蒡、蒺藜、苦杂草等。杂草显然与这片土壤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因为这片土壤长期以来一直让文明社会的一朵黑色花朵——监狱——在上面生根发芽。幸运的是,在大门的一边,几乎就在门口,真的长出了一丛野玫瑰。今年六月,像宝石一样娇嫩的花朵出人意料地绽放,让人想象它们是在给走进监狱的犯人或走出监狱走向刑场的死囚送去温暖和魅力,以此来表达他们在对真诚的同情和善良[1]
《红字》从一群闲人谈论一个被监禁的通奸者开始。从叙事形式来看,这部小说体现了一个主要的冲突——个人努力实现的救赎与社会强加的救赎之间的差异。霍桑描绘了一幅强烈的社会否定的画面,其效果或功能是使个人选择更具吸引力。这种选择被恰当地描述为隐藏在一扇敞开的门后。毫无疑问,人们会觉得这篇课文包含着潜在的文字。《栎木"大门上沉重的铁锈》以其斑驳的姿态告诉读者,这里封闭的世界在建筑上已经非常古老,这表明将要出现在监狱里的心将与新英格兰土地上现存的文化一起屹立在对,但这颗心的异国情调可以与门廊上“野玫瑰”的精致相媲美。她像宝石一样珍贵,芬芳而温柔,美丽而宽容。一群“邪恶的植物”强有力地占据了这片小草原的大部分空间,并守护着“监狱”之地。在这个简短的空间描述中,霍桑展示了两种文化的对决定,微妙地延伸到对,社会对“出轨”女性的压制,也表达了对对激情在人性最深处的认可。尽管这种“野玫瑰”式的异质文化只能植根于“门槛”,没有土地让它有家的感觉,“野玫瑰”仍然为世界上“非法”的真爱欢呼。在对对“监狱大门”的描述中,美丑并重是对对社会多元价值体系的认同,隐含着社会话语权的变化和演变。在“你只管唱,我上台”的话语竞争中,让读者意识到“胜利永远在人们心中。”
2.在《红字》的“市场”一章中,作者通过描述一个人物活跃的空间的逐渐变化,明确地界定了海丝和特白兰的身份。故事发生在“200多年前,一个夏天的早晨,监狱街, 波士顿监狱门前的草地上挤满了人,他们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布满钉子的栎木大门。”[2]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公共空间里,霍桑后来写道,“来观看的人总是摆出庄严肃穆的姿势,这与他们的身份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宗教和法律几乎完全是一体的,两者在性质上完全融为一体,不分彼此。”[3]这种公共空间与法律的代言人没有什么不同,代表了一个特殊社会的价值评估体系。那时,从监狱大门到市场没有多少路。然而,根据囚犯的经验,这可以算作一次长途旅行;尽管她骄傲地向前走,但她每走一步都感到一种巨大的痛苦,仿佛她的心被扔到了街上,让别人唾弃和践踏。在这个阶段,特白兰,海丝,几乎平静地处理了她在对遭受的折磨。她由邢台走到市场的西端。邢台几乎是建在波士顿,最早的教堂的屋檐下,就像教堂的附属建筑。[4]
海斯特白兰自豪地行走在一个不长的线性空间里。在这个与他人共享的空间里,她享受着对生活的审美体验。事实上,这个邢台是整个惩罚机器的一部分。从过去的两三代人到现在,它只是我们心中历史和传统的纪念;但在那些日子里,它就像法国恐怖分子的断头台。人们认为它是教育人们弃恶从善的有效工具。简单地说,这个邢台是一个颈手枷的平台,上面立着颈手枷以示惩罚,而这个枷套紧紧地钳住了人们的头和脖子,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期待它。这个由木头和铁制成的刑具充分体现了羞辱人的思想。在我看来,没有比这更违背我们普通人人性的暴行了;不管一个人犯了什么错误,没有什么暴行比不让罪人因羞愧而掩面更邪恶、更残忍,因为这是这种惩罚的本质。[5]
女主角的形象在公共空间逐渐清晰。这个公共空间就像一个开放的法庭。越是气势磅礴,缺乏语言的矛盾就变得越明显,越成问题。这是一个公共空间,暴露和隐藏,真相和虚伪并存。有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每个人不仅会感受到这种冲动,还会受到周围人的感染。在教堂里,这种冲动已经难以抑制,但现在在一个空虚的世界里,它咆哮着冲向天空。在这里,人群涌动,情绪激昂,足以产生比风吼、闪电吼、海浪吼更震撼的声音;许多人的心连在一起,成为一颗巨大的心,形成一种团结的冲动。同样,许多强有力的声音融合在一起,造成巨大的噪音。[6]
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固定在这个互文的公共空间里,反映了双重对的张力。在这个本应充满欢呼的脚手架空间里,欢呼声逐渐消失,最后变成了低语;在这个人们必须说话的地方,海丝特白兰只能无言以对;在这个必须自信地说话的地方,丁梅斯代尔变得越来越虚弱和苍白。他们的心总是向着人性中的神性前进。柏拉图曾经说过:“人最大的幸福是灵魂与神性的接近和统一。”霍桑显然让海丝特白兰成为了整个小镇的代表,这个公共空间的每个细节都保持了她作为中产阶级成员的尊严和优雅,成为了最幸福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