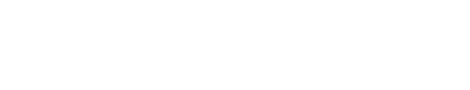简述寓言的教育意义(吊诡意义:略论《逃亡》的寓言图景)
胡耀恒教授认为高行健戏剧是哲学家的戏剧,而刘再复总是认为高行健戏剧是思想家的戏剧。在高行健的戏剧中,处境非常困难的人物不断地倾吐死亡、性和意义等沉重的字眼,影响了观众的视觉和听觉,远离了自我沉思的宁静。[1]4 吴晓东和对的现代派小说被描述为对读者的“治疗”,这也适用于高行健戏剧。高行健有意将戏剧的这一面和另一面割裂开来,尽力表现出普遍意义缺失的荒原场景,使其具有一定的寓言性。
《逃亡》,两男一女从大屠杀现场匆忙逃到一个放有杂物的仓库,但他们无法结成联盟,相反,他们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相互争斗,就像萨特《禁闭》中的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这三个男人彼此不和,他们的性别对升级为身体冲突。仓库成了他们的避难所,同时也成了他们相互攻击的战场,这与机枪和扫射的声音相对应。声音成为这个封闭世界中唯一直观的媒介,整个舞台的黑暗背景预示着世界末日的来临。多声部语言构成了高行健戏剧的主要支撑,而语言则绑架了意义或意味着间接语言。《逃亡》的戏剧语言已成为“肢解、侵蚀和扩散的代码”,这已成为对对,现代人终极意义缺失的直观观察,从而获得了寓言价值。
我不喜欢诉诸政治理论和诠释哲学的戏剧,就像文字的美和文字的游戏是诗人的事一样。戏剧有戏剧语言,它通过声音而不是语言直接唤起观众的感情和联想。这种有声语言应该成为剧院里的有形现实。当然,我的戏剧也玩语言。首先,这是一个声音的游戏,而不是意义的游戏。[3]275从这个宣示性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高行健有意追求语言和意义之间的弹性空间。——句子和意思都是真实情感的传递。然而,经验的非现实性导致了语言的转换,这最终是对对语言的嘲弄。在《逃亡》中,年轻人偏执的革命理论,中年MoMo的逃避哲学,甚至年轻女孩的独白都是自成一体的,但是它们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面对对,年轻人的革命言论,中年人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表达了他们的逃避哲学,试图说服年轻人承认革命的荒谬和无意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中年人宣称,“我必须有我自己的个人意志,独立的意志,独立的意志.我逃避所有所谓的集体意志”,但当对,的年轻人当面问我时,他只能用“我只是一个路人,偶然路过,偶然卷入,偶然激动,偶然说几句话,如此而已”的偶然哲学来逃避责任。精神清洁只会给你带来虚张声势,但在现实中却无法平静。在对方言中,中年人和女孩一起卸下冰冷的盔甲,试图扮演女孩的父亲。对,是个中年男人,对年轻男女有不同的态度。对视前者为居高临下的教育家,而年轻人则与对,针锋相对,处于水火之中。“高行健”的文学作品常常充满了一种‘围城心态’。剧中人物认为“对在全世界都没有好的意图”,其他人也做不到这一点,两者都没有帮助,所以他感到空虚和孤独,他不能永远活着。生存是一个永恒的困境。”[4]203语言游走于现实与虚幻之间,徘徊于感性与诡辩之间,构成了中年人话语中的多声部。他的逃避哲学似乎是清晰的,它被隐含了。——“生活总是在逃亡,如果你不能逃离政治压迫,你将会逃离他人和你自己。一旦这个自我觉醒,最终也正是这个自我无法逃脱。这是[5]109个字符的裂变与其他人的异质语言交织在一起,破碎的语言片段与仓库铁门外的声音相对应,制造了舞台的噪音和不安。所有声音的兴奋揭示了生存的凄凉景象。
多声部对剧中人物的争论包括对大师、妥协和不相交的谈话。在第一幕的后半部分,剧中的三个人沉浸在各自的思想世界中,暂时放松了紧张的神经。这三个人试图在对过去的回忆或未来的幻想中找到一种存在的感觉。这种记忆“不仅是沉湎于过去,寻找过去的自我,而且是确认和救赎对现在的‘我’,是建构‘这个存在’的方式,使记忆从根本上与过去的‘我’无关,而恰恰与现在的‘我’有关。”[1]64个女孩把性作为自己的支撑点;中年人的梦幻无意识暴露了自己的弱点,“我只是一个路人”的雄辩被“你总是走在深深的泥淖里”的哨声所代替;年轻人摆出革命的信念,沉溺于对性的感性描述。幻想和记忆成了三个人的临时避难所,而临时屏蔽危险的代价是,在和平被打破后,三个人不知所措。年轻人“一文不名”,完全打破了由三个人用回忆或幻想建造的乌有之乡。年轻人突然醒来,逃离幻境,试图抓住现实中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就是逃离仓库和死城。女孩拒绝了这个毫无意义的举动。在她看来,还不如“让自己沉浸在心里".”这种精神上的自我淹没是一种精神上的逃避。中年人的自我追问徘徊,“就这样,在黑暗中”,与年轻人的鲁莽没有关联,不敢轻易踏出,无法在记忆中确认自己,生存的焦虑萦绕心头。面对对女孩的指责,中年人不知所措:“面对死亡,我们不是英雄、懦夫、圣人,只是傻瓜.十足的傻瓜。”在高行健的戏剧中,混淆的词语随处可见。高行健似乎不擅长哲学思考。在他看来,“矛盾、混乱和意义的模糊是思想的起源”。[3]26戏剧《高行健的对》与其说是对对生活哲学的传播,不如说是对对生活经验的再现,这是一种传达他自己生活经验的生活感受,即使这种经验是“毁灭性的经验”,它将粉碎他的过去和现在。在对人物语言进行自我解构的同时,一场关于生命图景的旅行开始了,“经验”语言徘徊在字面语义和弦外之音中,就像生命图景的混乱和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