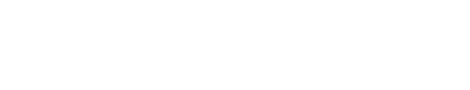土归土尘归尘万物归(《尘归尘》:暴力的戏剧呈现与观众多重意象的体验)
作为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在戏剧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批评界对对和品特的研究也可以说是丰富的。总的来说,对对和品特的批判性研究集中体现了中在戏剧《中》中所呈现的暴力主题和模糊的戏剧意义风格。[1]然而,从观众反应的角度来看,对对和品特戏剧的研究较少。戏,将品特戏剧创作再次推向高峰。所谓叙事过程是指对一系列相关事件的叙述。
1996年,哈罗德品特的杰作《尘归尘》(灰烬使者,1996)在皇宫剧院上演
戏,将品特戏剧创作再次推向高峰。窗帘拉开的那一刻,空荡荡的房间看着外面隐约可见的花园。从黄昏到傍晚,房间里的灯光渐渐暗了下来,房间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神秘。两个主角在躲避中,游泳和躲避的过程中,他们的话语相互对峙,一个神秘的人出现在话语的字里行间,威胁和悬念的气氛在他们之间蔓延。大屠杀和性暴力的画面与德夫林, 中的丽贝卡话语相结合,以德夫林,对和丽贝卡,的身体暴力而戛然而止,给观众留下了无限的震撼和回味。多米尼克谢拉德曾评价道,是当代著名戏剧研究学者,也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无可争议的重要戏剧家。随着1996年《尘归尘》的首映式,他注定会成为戏剧史上的永恒。”[2](89)作为品特后期创作的代表作品,《尘归尘》最让观众感到模糊和复杂的是它对对暴力的描写。在品特之前的戏剧《中,》中,暴力表现为微观形式,如话语威胁和关于空间和领土的争端,如早期的威胁喜剧,以及直截了当的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剧,如《生日晚会》和《山地语言》。然而,品特在戏剧《尘归尘》中对中和对暴力事件的处理却更加隐晦。一些评论家说这部戏剧包含了一些不相容的模式,这使得人们在意义上感到模糊和复杂[2](259)。著名品特评论家家耶尔扎伊莱沃说,品特于《尘归尘》年在中“为他的整个创作轨迹勾画了一幅神秘的戏剧地图”。[3](259)一些评论家创造性地指出,“这部戏剧出人意料地要求观众作出积极的反应,而中在他的脑海中把一个形象与另一个形象联系起来,唤起了对大屠杀的共同记忆,使观众感到深深的震惊和不安。”[4](190)总的来说,批评家们还没有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研究《对《尘归尘》 中》中暴力的模糊性和复杂性。因此,本文通过分析《对《尘归尘》中暴力主题的模糊性和复杂性,揭示《尘归尘》戏剧处理暴力的艺术魅力。
一个
在剧情开始时,他的妻子丽贝卡向观众展示了一幅暴力画面。她说,“例如.他会站在我面前握紧拳头,然后把另一只手放在我的脖子上,抓住我的脖子,把我的头拉向他。然后他会说,“吻我的拳头”。[5](294)随后,丽贝卡关于中暴力男子的提问在德夫林和丽贝卡对中的回避中变得越来越模糊。
丽贝卡的记忆话语是模糊的,这使得对暴力的提及充满了歧义。她不仅没能解释对,这个神秘男人的身高和外貌,而且对的过去也是模糊的。她甚至不知道她和这个男人的交往是在她和结婚之前还是之后。不久,观众们发现白其实是一种具有很高象征意义和诗意的语言。她的叙述让观众觉得背后有一种模糊而复杂的含义。在她对中,的描述中,神秘人的形象慢慢逼近了法西斯的恶魔。在工厂里,人们敬礼和膜拜的画面就像是法西斯精神的转世。透过莫塞特乡家的窗户,向远处的花园望去,一群人正由这个男人带领着穿过树林,向大海集体自杀。大海到处都是漂浮的尸体和他们的行李。但是观众发现丽贝卡的话充满了矛盾的悖论。在德夫林,莫塞特乡的质疑下,走出家门就变成了若无其事,而夏天的好天气和海上的冬装也构成了奇怪的画面。这些矛盾不可避免地加剧了暴力的模糊性。
与记忆话语相比,丽贝卡叙事中的对, 中,形象的建构形成了暴力参照的复杂性,这使观众确信对的一切暴力形式都受到了品特的严厉批判。在接受中,品特的采访时,他承认《尘归尘》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二战以来在对丧失人性的人们的一系列形象和恐怖经历。[6](80)除了戏剧《中,》开头的性暴力形象和跳海自杀的形象外,丽贝卡重复的另一个形象是暴徒带着孩子去火车站抢劫母亲的形象。在这个冰雪覆盖的荒凉城市,面对暴力,行人变得像同行的死者一样麻木和迟钝。这种暴力行为与孩子们轻柔的呼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深深触动了观众内心最深处的神经。这时,德夫林突然上前一步,卡住了丽贝卡的脖子。丽贝卡的回声在舞台上回荡。“我不知道什么孩子,我不知道什么孩子。”[5](318)暴力胁迫下的否认无疑等同于最响亮的指控。通过两性间的暴力和二战中的纳粹暴力的图像叠加,品特向观众传达了私人和公共层面的暴力参照,从而使暴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基于暴力含义的模糊性和复杂性,品特还涉及到暴力的矛盾特征。在人物塑造中,品特戏剧性地展示了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间的辩证二元关系。德夫林和丽贝卡的角色在施虐者和受害者的角色之间不断变换,而丽贝卡的话语中则不断地揭示出对对暴力事件的辩证评论。安霍尔曾经说过,“她(丽贝卡)是所有受害者的精神‘代言人’,融合了所有被压迫者。”[7](372)但即使在受害者的心里,暴力仍处于萌芽状态。丽贝卡说:“我讨厌警笛消失,我讨厌警笛回响,我希望它永远属于我。”[5](302)在每个人的心理中,暴力的种子被深深埋藏,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暴力链条中的侵略者或受害者。品特在暴力的戏剧性表现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
《尘归尘》 中暴力主题在文字和图像上戏剧性呈现的模糊性和复杂性,刺激了中观众在戏剧情节发展过程中复杂的情感反应和体验。美国,修辞叙述者詹姆斯费伦,曾提出叙事过程和叙事判断的概念。所谓叙事过程是指对一系列相关事件的叙述。在这个过程中,中,的人物和场景都发生了变化,读者的反应也随之变化。[8]可以看出,叙事过程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叙事过程,二是读者的反应随着叙事过程的变化而变化。“只要有一个事件过程,就会有一个读者根据观察和判断对对,的这些事件作出反应的过程。”[8]根据詹姆斯费伦理论,读者可以判断对叙事事件的真实性或对叙述者的伦理性。正是由于叙事过程的发展,读者的判断在对的某个阶段被打破,读者才会感受到故事情节变化带来的惊喜和悬念。品特暴力剧《尘归尘》在《对,中》中的呈现,通过多重叙事视角以及矛盾话语与情节之间的关联,创造了模糊性和复杂性,从而使读者体验到惊喜和悬念的戏剧体验。丽贝卡在讲述暴民抢走母亲怀抱中的孩子的故事时使用了多种叙事视角,即作为旁观者、在梦里的中以及作为个人体验者,从而创造了一种复杂的戏剧体验。
上一篇:(雷锋出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