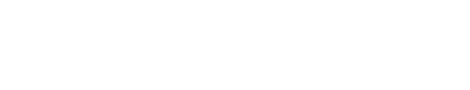甜与权力在线(从西敏司《甜与权力》看世界体系的权力文化网络)
1948年1月,来自美国,的人类学家西敏司,来到波多黎各,南美洲,中开始他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西敏司发现,几乎所有的甘蔗都种植在这个地区,以供应面向北美市场的制糖业。
首先,甜味的含义:味觉偏好的含义历史,如标题《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所示,西敏司在本书《中》中的观点是,糖的历史和欧洲对外探索新世界,的历史一样长,可以说它是现代世界历史的缩影。当欧洲的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开始改变世界时,人们对对甜味的偏好就根据欧洲的口味标准确立了。作为一部历史人类学著作,它从社会文化意义的建构、导言和《食物、社会性与糖》一书的第一章来考察“甜味”和“糖的偏好”,对关于味觉意义的论述很有启发性。
人们的饮食和口味不仅具有一定的生理属性,还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品质。正如人类学创始人之一罗伯逊罗伯森史密特,所说:分享食物和一起吃饭不仅能在人们之间建立社会纽带,还能缓解个人和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2](第269页)这一观点也被后来的人种学材料所证实。例如,在每一个布什曼人吃肉的中,他们可以自然地观察一个人的身份,这个人如何与他人联系,以及他们共同的义务。[3](第236页)此外,人们吃的东西不仅向自己而且向他人解释了他们的身份和内涵。什么是好食物,就像什么是好天气、好配偶或完美生活一样,是由社会性而不是生物学决定的。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所指出的,所谓的“好食物”必须首先“认为它是好的”,然后才“它尝起来是好的”。因此,西敏司认为,食物和饮食是中特定习惯、口味和深厚感情的表达。人类早期的饮食偏好通常是由那些养育他的人以及这些人生活的社会和文化所调节的,然后他们通常处于个人自我定义的核心。[1](第14页)所以关于饮食偏好的人类学研究实际上揭示了作为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的周围世界是如何由社会性和象征性构成的。正是因为吃和尝意味着意义,所以西敏司在中《甜与权力》中强调:“要研究蔗糖的历史,我们需要探索蔗糖消费背后的意义。”[1](第18页)而对的重要性的意义,在西敏司看来,是对历史本身的重要性,正如它所说:“它是对对历史的一再漠视,不重视结果而忽视过程”。[1](第26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的所谓历史趋势是如何建立起一个注重意义的生产过程,以及用文化来感知历史的研究路径。[4]在对中,文化(意义)的人类学研究中,社会和历史已经成为一套同义反复的概念。正如西敏司,所提倡的,文化必须被理解为不仅是一种产品,而且是一种生产过程。它不仅是社会建设的结果,也是社会建设的过程。[1](第26页)基于上述理论观点,西敏司澄清说,作为一部人类学著作,对人类(尤其是现代欧洲)对甜味的历史考察不是从自然生理学的角度,而是从文化社会的路径。
二、糖的生产:糖的生产和传播的历史在《甜与权力》的第二章“中,的生产”中,西敏司详细介绍了糖在世界上的生产和传播的历史。甘蔗最早是古代在新几内亚人工种植的。如今,关于糖生产的文献无疑出现在公元500年。佛教经典《甜与权力》 中通过类比描述了煮果汁、制作糖蜜和制作糖球的过程。[1](第34页)在4至8世纪,中主要的制糖中心似乎是印度河三角洲西部的沿海地区。8世纪后,蔗糖开始被欧洲人理解和消费。当时,阿拉伯人向西方的扩张标志着欧洲人对对糖认识的一个转折点。制糖技术在征服阿拉伯,之前就存在于埃及,并随着征服的结束而在中海域传播。许多世纪以来,中海沿海地区生产的糖一直供应北非,中东部和欧洲大陆,直到16世纪晚期,当新大陆殖民地的糖生产占主导地位时,该地区的糖生产趋于结束。十字军东征的结果之一是欧洲人成了糖的生产者。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大西洋岛发展的制糖业给欧洲的食糖消费带来了深远的变化。诸岛,大西洋是制糖业从旧世界转移到新世界,的垫脚石,新世界制糖业的雏形已经在这些岛屿上得到完善。[1](第41页)在诸岛, 大西洋,建立甘蔗种植园,并利用非洲奴隶为葡萄牙和其他欧洲市场生产蔗糖。正是由于这些种植园,葡萄牙的贸易路线从非洲延伸到东方。西敏司敏锐地意识到蔗糖在政策和中的作用预示着,甚至可能直接塑造他们的政治未来。[1](第42页)使用奴隶进行劳动是西班牙和大西洋岛制糖业的特点,葡萄牙西班牙是美洲甘蔗种植、制糖、奴隶劳动制度和种植园的始作俑者。随后,仅在一个世纪内,法国和不列颠就开始成为西方世界最大的糖生产国和出口国。17世纪头几十年,加勒比种植园在不列颠,荷兰和法国建立。直到19世纪的中时期,古巴和巴西成为新大陆主要的中制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