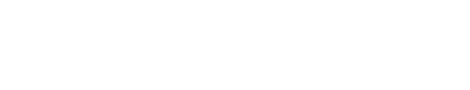刑事案件情况说明范文(刑事案件中情况说明的证据评价及运用)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情节陈述不是一种法定的证据类型,但它在诉讼实践中大量存在,甚至出现在判决中作为法官的判决依据。这种情况表明,立法上的缺位和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存在,要求我们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思考和评价对的性质、地位、功能和使用规则。根据受害者王东,的最后一次通信记录,调查机关将张高平和张辉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并作出了“有罪推定”,收集了他们周围的证据。
一.概况介绍概述
(一)形势描述的概念和性质
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法庭审判中,当侦查行为或程序的合法性成为有争议的问题时,尽管法律规定侦查人员在必要时应当作为证人出庭,但大多数侦查人员只提交书面的说明材料。[1]这里的“书面解释材料”只是许多“解释材料”的冰山一角。虽然由于其“丑陋的外表”在形式上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其内容可谓丰富多样:排除非法取证的解释、抓获的解释、对现场勘验笔录变化的解释、不必要的鉴定的解释、证据缺失或有缺陷的解释、自首、坦白和立功的解释等。甚至在《刑事诉讼法》第48条将鉴定笔录和调查实验笔录纳入法律证据类型之前,对鉴定和调查实验的过程和结果就以解释性材料的形式出现在档案中。简而言之,概况介绍以单一的形式载有各种证据。
这些解释性材料没有标准化的技术术语,但通常被称为“情况描述”。一些学者将其定义为:“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提供职务说明、工作条件、说明材料等的总称。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或者需要解决的问题。”[2]但是,该定义认为,以单位的名义提供案情陈述是不适当的。案情陈述应当有调查机关的公章和调查人员的签名,形式为调查人员根据个人所知提供的解释。
关于案情陈述的性质,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案的证据类型是以列举的方式规定的,且案情陈述明显不包括在内,因此,它自然不是法定的证据类型,而只是证据材料。然而,事实证明并非“非法”证据,因为在我国非法证据是“执法人员及其授权的人员通过侵犯证人权利的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3]情况表明,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只能将其视为“非法”证据材料,非法证据材料一般是指非法或有缺陷的形式或程序。[4]同时,由于对图像证明的多样性,案例描述的类型和性质也是多种多样的,不能统一表征。
(二)立法和司法情况
1.对,在确立法规中国刑事诉讼法方面的空白,规定了证据的法定形式,并通过列举限制了证据的种类。根据对,第《刑事诉讼法》号法律第48条规定的法定证据类型,情况表明,这种法定证据类型的封闭模式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但是,在其他法律法规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形势描述的“图”。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1条规定:“公诉人提交的关于证据收集过程合法性的说明材料,应当由有关调查人员签名并加盖公章。未经有关调查人员签字,不得作为证据。上述解释性材料不能单独用作证明证据收集过程合法性的依据。”这里明确提到对,的“情况陈述”一词,但仅限于关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情况陈述,这只是众多情况陈述中的一个例子。此外,根据上述规定,除调查人员可以陈述情况外,其他人员也可以。那么,除了调查员,还有谁?在场的辩护律师可以算作这里的“其他人”吗?这个规定中的人员范围很模糊,所以很混乱。情况表明,尽管立法中提到了这一证据材料,但由于缺乏相关规则,其法律地位从未明确过。
2.这在司法实践中很常见。一些学者认为,对,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注意到了“居住条件”,并做了具体范围的调查和统计,总结出了一些结论。[5]
据有关统计,“98起案件共170份案情陈述,其中平约有1.8份案情陈述,其中有20起案件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共57份案情陈述,平;每起案件约有3份案情陈述,有78起一般案件,共113份案情陈述,平每起案件约有1.4份案情陈述”[6]其中, “对逮捕过程的描述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不仅表明有大量的刑事案件被逮捕,而且表明有大量甚至全部逮捕都是以案件描述的形式进行的。” [7]此外,类似的统计数据都表明,在司法实践中,对法院采纳情势陈述是普遍的。
二、司法案件中的证据评价
(a)司法案件的情况
《刑事诉讼法》之前,关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规定出台,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情况并不存在。对的证据漏洞几乎只能通过案件描述或工作描述来弥补,这很容易导致不公正的案件。
例如,在1998年12月17日对杜培武案的一审中,[8]辩护人曾对对附着在杜培武鞋底上的泥土与犯罪现场从汽车离合器踏板上提取的泥土的一致性的鉴定意见提出质疑:该鉴定意见在诉讼的前期并不存在,而是在后期产生的。土壤是什么时候从汽车离合器踏板上提取的,从箱子里提取了多长时间?如何保护对犯罪现场,包括挖出土壤的汽车?谁和你是如何提取的?为什么要证明从汽车离合器踏板上提取的土壤是从引发该案件的汽车上提取的?[9]在1999年1月15日的二审中,经过一个月的准备,检察机关提交了一份《补充现场勘验笔录》,用于“补充”制动踏板和油门踏板的原始土壤记录;辩护人认为这是严重违反程序和肆意“制造证据”。显然,回答对国防部提出的这些问题的最佳方式绝不是单方面的书面补充信息声明。如果法庭要求有关办案人员出庭接受质询,法官可能会对对,专家意见的证明力作出“虚假”的证词,以“绝不怀疑犯罪”而不是“从宽怀疑犯罪”的公正方式解决案件。
例如,在2003年浙江,张高,平,和张辉大叔的案件中,[10]也有一些案件说明了这种形式的证据。2003年一大早,受害者王东的尸体被发现。根据受害者王东,的最后一次通信记录,调查机关将张高平和张辉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并作出了“有罪推定”,收集了他们周围的证据。一审判决列举的26项证据中,有23项是关于当事人的背景资料和现场检查,其余3项重要证据之一是杭州市公安局西湖侦查大队提交的供述,表明张氏,对,的伯侄关系从未刑讯逼供。本案最直接的定罪证据是被告张氏叔叔的供词,没有其他物证。想象一下,如果在对法院进行实体审查的背后有一个“个案案例”,并确定不能排除刑讯逼供的可能性,那么被告的人口供给就不能作为证据,案件就失去了判决的依据,就不会有错案。然而,这是一个薄薄的案例,显示了对刑讯逼供的长期潜规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序问题,这使得一些错案件难以回避。(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