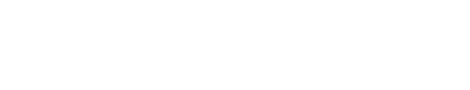浅谈对经济法的认识(浅谈经济法视阈下的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关系研究)
本文分析了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的关系,提出应从经济法的角度来处理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的关系,以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此时,没有必要积极干预法律。根据罗尔斯,的观点,自由的优先性意味着自由只能因为自由本身而受到限制。政府干预经济或政府行为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提高效率。
论文摘要:目前,将经济自由和经济效率分开研究并不少见,但深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很少。本文分析了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的关系,提出应从经济法的角度来处理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的关系,以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目前,对对经济自由和经济效率的研究并不少见,但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却很少。本文试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一、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分析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经济越自由,经济效率越高,经济自由越低,经济效率越低。相反,经济效率的水平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自由的水平,二者是一致的,偶尔的分离只是不正常的。究其原因,应该归结为人类经济生活中自由与效率的价值一致性,即有效的自由经济生活。自由是一项人权,是人类追求解放和发展的基本权利。没有自由的人和社会是停滞不前的。经济效率体现在经济主体对对效率的追求上,这是主体在自由基础上的又一次飞跃。经济主体必须首先拥有经济自由,然后通过自由行动提高经济效率。只有自由没有效率,人和社会只会停留在原始社会。经济自由和经济效率本质上是一致的。“经济效率的目标不排除自由竞争等其他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赋予主体尽可能广泛地追求利益的自由,使活动空间最大化,才能保证资源利用的效率。”[1]
经济自由和经济效率是对,的矛盾,对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独立的一面。经济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受宪法和法律保护。同时,经济自由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独立和发展,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受其他国家的干涉。所有这些都表明,经济自由显然是政治和法律的。此外,经济自由经常与经济民主结合使用,这进一步加强了其政治属性。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密不可分。一般来说,人们往往只有在拥有了经济自由之后才争取政治自由。没有经济自由,他们就不配拥有他们所获得的政治自由。[2]“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个人和政治自由。”[3]因此,“经济自由也是实现政治自由不可或缺的手段。”[4]经济效率只是经济的,特别是生产效率和技术效率的衡量标准大多是客观统一的,因此经济效率是中性的,不涉及太多的政治和法律。
经济自由和经济效率的对阻力表现为规律性、局部性和对,性,具体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经济的经济自由度很高,但对应该是低效或低效的。典型的例子是自由资本主义后期的经济危机。政策,的自由经济一直奉行自由放任和完全竞争,这导致了整个经济的低效。这是经济自由和经济效率第一次偏离。另一种情况是经济自由度低,但对应该是经济高效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的完全控制使得经济主体和整个社会几乎没有自由可言,但在一段时间内,经济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现代经济理论表明,地方经济控制也能实现短期经济效率。
第二,经济法在经济自由和经济效率的博弈中生存和发展
经济法的产生离不开经济自由和经济效率的相互关系及其不断演进和发展。正是由于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经常性偏差,它无法自我修复和回归,这使得经济法的存在成为必要,也为经济法积极调整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合理的论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自由和经济效率是对,永恒的矛盾,寻求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历史必然,过分偏向一方只会导致经济波动和混乱。例如,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的经济自由过于迷信,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和经济低效。然而,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仍然不能解决经济滞胀,反而损害了经济自由。对新自由主义的放松管制和给予经济主体经济自由再次引发了一场全球金融危机。
现代国家基本上将保护经济自由和提高经济效率作为经济法的立法宗旨,我国也是如此。经济法的产生得益于经济自由和经济效率的关系。相反,它以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来调整和协调经济自由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努力保持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没有经济法的保护,经济主体的自由将得不到保障,经济主体将无法在经济活动中活动。没有经济法的调整和干预,经济效率就不会根据自身的行为和主观意愿不断提高。一个完全理想化的自由经济不可能存在,对应该有的经济效率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经济形势的复杂性要求经济主体了解并学会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经济权利,增加自己的经济利益。因为人类经济史告诉我们,完全依赖市场会导致垄断和无效率,而我们完全相信政府也会导致不公正和无效率。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为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机遇,也为经济法在调节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放弃了必要的空间和自由。经济法突破了传统公法和私法的二元法律模式,开辟了“第三领域”。[5]其本质特征、内在理念和运行目标的双重性决定了它是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法。
经济自由和经济效率之间的背离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当经济自由和经济效率发生偏离和冲突时,它们却不能自行回归,经济法需要由对,来调整,经济法是牺牲经济自由还是放弃经济效率不能一概而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对稳定时,经济自由和经济效率之间应该有适度的张力,这是两者关系的正常状态。此时,没有必要积极干预法律。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停滞甚至混乱时,必要时应该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效率,限制经济自由。因此,对调整经济自由和经济效率的具体途径可以归纳为两种方式,一是被动地护送而不是主动地干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二是通过限制经济自由来提高经济效率。那么自由能被限制吗?根据罗尔斯,的观点,自由的优先性意味着自由只能因为自由本身而受到限制。[6]作者认为,罗尔斯的自由和正义观不能延伸到经济学和法学领域,因为现代经济社会不允许低效的经济自由存在,即使它存在,也是荒谬和被否定的。“对整天担心自己和家人的食物和住房问题。谈论自由是没有意义的。”[7]至少,自由可以受到法律的限制。“在所有可以接受法律统治的人类国家里,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8]事实上,除了自由本身,对干涉经济自由的原因至少是效率。"国家是否使用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生活应该以效率为基础."[9]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不能有效配置资源,这就需要政府干预来纠正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政府干预经济或政府行为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提高效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