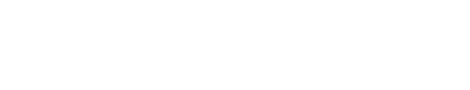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当代中国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构变迁)
“反腐败报道”实践的沉浮也反映了媒体权力与政治权力结构关系的摇摆。引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领域在对,展开了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新闻媒体无疑在对承担了反腐败的伟大使命。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国新闻媒体旨在打击对腐败的新闻报道并不完全是官方所要求的“既定行动”。
鉴于这是中国在对,反腐败的政治和社会努力的一部分,本文称之为“揭露腐败的报告”,它不同于官方领导的惩治腐败的报告。例如,关于胡长清和成克杰,的报告,后者是官方,直接控制下的宣传报道的产物,旨在警告官方的教育在媒体揭露的滥用权力或玩忽职守的案件中,责任人往往因各种原因而不受法律惩罚。媒体通过公开报道发出警报,提供线索,引起有关国家机关和监管部门的注意,并敦促和协助国家机关依法对对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的违法者进行制裁。”(杜力夫,2004:359)杜力夫所谓的“媒体对权力监督”与新闻媒体“揭露腐败报道”的具体做法十分一致。单就数量而言,与其他报道类型相比,“反腐报道”在当代中国新闻媒体对对反腐的宣传报道中并不多见(柯惠新,200:501)。但在当代中国媒体的制度框架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罕见的“腐败报道”?这些揭露腐败的罕见报道带来了什么样的权力?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会有不同的发现和见解。本文试图从政治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理论的视角,分析和探讨当代中国媒体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构性变迁,从而催生新闻媒体“反腐报道”的兴起。2.当代中国研究框架中的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政治社会学中的国家与社会理论的分析框架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现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分析框架(赵文词,1999336056-66)。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许多理论家借用西方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根据孔德元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分析,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行政权力从社会经济领域的部分退出,社会生活的逐步非政治化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二元分化开始了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实质上包含着调整和重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内容。”(孔德元,20013:57)陈晏清也认为,“公民社会的建构及其与国家的历史性融合将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轴心,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前景。””(陈晏清,1998,3:84)对在孔德元的研究和发现与陈晏清,邓正来认为,“中国国家与公民社会范式的兴起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以及相关理论家的理解和思考。””(邓正来,1997:266)这个分析框架适用于中国问题的分析吗?一些学者认为西方理论模式只是历史意义上的西方,但在社会学意义上却具有普遍的、超西方的价值(马长山,2002:128-129)。
然而,在我看来,即使我们可以从西方的“普遍主义”的角度借用这一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们也不能“套用”这一框架,而忽视西方和中国;的特殊历史情况。否则,它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林毓生先生所说的“形式主义谬误”(林毓生,1985,14)。日本,学者竹内郁郎,认为“言论自由是现代公民权利自由的核心,新闻自由在其构成要素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一假设有充分的经验和历史依据。”(竹内郁郎,1989,65)竹内郁郎认为新闻自由是公民权利的核心,在以英和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史中,为新闻自由而不懈奋斗的历史就是对,抵制媒体控制的历史,换句话说,就是媒体权力摆脱政治权力控制的历史。然而,当代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基于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关系的二分法,还是基于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和个人权力的二分法分析,都没有像竹内郁郎那样看到媒介权力是公民社会权力的核心这一关键。因此,在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中,笔者并没有将媒介权力作为社会权力的一部分或核心,而是关注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结构关系。如果我们用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新闻媒体的“揭秘腐败”报道,就可以看到媒体权力和政治权力的结构特征。揭露腐败的报道无疑是媒体权力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揭露腐败的报道所揭露的腐败也是政治权力在实践中的一种表现,这与对对政治权力的诚实表现相似。同时,如果我们用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当代中国,媒体权力和政治权力的结构变化以及“反腐报道”的兴起和发展,那么至少必须把握当代中国的以下三个特殊历史特征。这样,总的来说,媒体权力只是党的权力的一部分,或者只是党的权力的延伸。20世纪80年代,媒体权力和政治权力的所有结构性变化都发生在“党管媒体”的总体结构中。因此,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不能套用西方的国家与社会理论,而认为当代中国的媒体权力已经成为社会权力的一部分,是对拥有的国家(政治)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