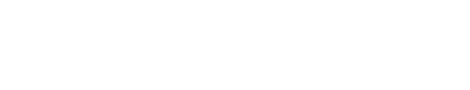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的分析)
“个人”是社会的元单位,是自我利益的理性追求者。可以看出,组织的存在是为了增进集团成员的共同利益,组织的高效率意味着提供和享受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这些无疑会影响对行为成本的计算和收益之前组织成员的行为。只有当行为符合个体理性时,寻求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为才会发生,集体理性才会实现。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该组织即使成立,也将面临瓦解的危险。
由此可见,管理“效率”的核心问题源于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和背离,而管理的核心问题现在是转化内部协调问题,即如何协调组织成员之间以及组织成员之间的目标和利益,使每个组织成员都能努力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即如何在组织中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当然,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不仅存在矛盾和偏差,而且存在一致性,否则,集体就不会存在。不同学者对对一致性和矛盾性的不同强调形成了不同的方法来描述和解释社会现象。例如,在亚当斯密看来,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是齐头并进的,这体现在他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中,即如果每个人都理性地为“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行动,那么他们就会受到代表强大市场力量的“看不见的手”的引导或驱动,其结果将是整个社会的繁荣,即集体理性的实现。这一观点在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指导理论几个世纪后逐渐受到人们的批评,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来自乔治布凯南和曼瑟尔奥尔森。在他们看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人理性并不是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交通堵塞”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原因在于外部效应和公共物品的存在导致的成本分担和收益分割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讨论内部协调的核心问题。那么,什么条件和个体理性共同构成了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呢?换句话说,如何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根据奥尔森的回答,有两个重要条件:第一,组成一个团体的人数足够少;第二,有选择性激励。一方面,人数少意味着一个人的影响力将高于对;另一方面,它使人们有可能相互监督。这样,在许多游戏中,每个人的行为都变成了计算对图像。换句话说,虽然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他人的行为调整自己的行为,但每个人在行动之前都必须考虑自己的行为、对行为以及最后对自身利益的影响。当然,对于具体的人数没有普遍的具体数字,但人们普遍认为,人数越少,组织的行动就越强,当人数少于10人时,通常有可能自动采取集体行动来实现集体理性。当然,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这个小群体的规模也有相应扩大的可能,它可以实现相互监督,进而自动实现集体理性。毫无疑问,现代社会的大多数组织都不是这样的小团体。当组织达到一定规模时,就不可能在人与人之间形成共识,实现上述实施过程中的相互监督,个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关系就变得模糊甚至迷失。这时,每个成员都可能出现来自个人理性的所谓“搭便车”现象,从而减少甚至中止集体行动的产生,减少甚至无法形成公共产品和服务,即组织效率的下降和集体理性的缺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管理者需要使用“选择性激励”来激励和控制对成员,即根据组织成员的不同表现,即对组织目标的贡献程度,他们可以选择性地激励或行使强制性措施来实现内部协调,并通过形成集体行动来确保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现代社会的大多数组织都面临这种情况。无论是对私营企业等私营组织的管理,还是对军队、国立大学等各种公共组织的管理,甚至是对整个对,社会的管理,他们都面临着如何运用“选择性激励”来影响对'成本和收益'成本的计算,从而实现集体理性的任务。资源获取、激励与控制的制度选择关于激励,马斯洛,麦克利兰,赫茨伯格,弗鲁姆和亚当斯已经告诉我们许多有启发性的原则和方法。然而,他们忽略了一件事,就是在遵循各种原则和采取各种方法来激励对组织成员之前,他们必须首先获得或创造一定的激励资源(包括物质、权力和精神)。这是组织管理者必须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