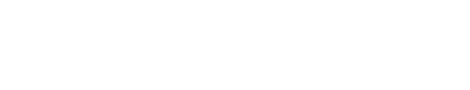学士学位论文(学士学位论文模板)
本文是一篇关于历史研究生论文的范文,也是一篇关于曹、西贝、鲁、史家、北鲁的自我检讨的范文。
漕溪北路40号原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在地。上海历史研究所的办公楼位于漕溪北路西侧,在今天的徐家汇图书馆和徐汇中学之间。这座四层楼的建筑面向南,是西式钢筋混凝土结构。它宽敞、明亮、宏伟。它也位于徐家汇。这是一个难得的黄金地段,在这里可以从噪音中获得宁静。那时,一群来自上海的著名历史学家聚集在这里。
一个
1974年初,作为《文汇报》的通讯员,在《文汇报》理论部主任张其成先生(1989年至1995年退休前担任《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的推荐下,我从上海一家企业进入了历史研究所。作为一名普通的年轻工人,脱产学习的机会非常少,我非常兴奋。丁凤林先生在报到时接待了我。他也是日夜与我们相处并组织我们学习和指导写作的老师之一。当丁凤林还是《解放日报》的高级编辑时,他只有36岁。1961年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他跟随陈旭麓先生攻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生。他不仅在史学方面颇有造诣,而且思维敏捷。他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家和作家,并写了许多专著,如《薛福成评传》。城市派他来组织和指导我们学习和写作更合适。
历史研究所大楼的底层是大厅和图书图书馆。图书馆里古籍线装书的数量相当丰富。倪金兰先生专门负责图书图书馆。当我们需要寻找信息时,我们经常会问资料室的古籍版本科学家杨·康年先生。杨先生很热情,经常为研究所的专家学者提供各种古籍和好书。他身材修长,脸色苍白,戴着一副旧眼镜多年。他有点虚弱。他对中国书法有渊博的知识。从13岁开始,杨先生就迷上了书,经常出入商店。作为一个成年人,他把所有的努力都献给了收集古籍。1944年7月,他毕业于无锡郭雪专业学校,主修三年制中文。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工作。为了丰富历史学院的藏书,他努力工作,到处旅行。他经常进出主要的旧书店和文物仓库。他不怕脏或累。他挑选书籍,分批运送到研究所。他是一个热爱书籍如同热爱生活的人。他不仅在书海中工作,还在家里收藏了许多珍本书籍。他胸中还有数百万本书。他不能回答任何关于图书版本的问题。在谈到早期历史研究所时,研究所的老学者们经常竖起大拇指,一致称赞杨康年是古籍版本的第一位专家。我从资料室借了几个小时的书,除了找书,大部分都是。
我在隋唐历史组的时候,方是明先生曾对我说,为了熟悉唐史,除了读《旧唐书》 《新唐书》,我还要读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的《资治通鉴》。我找到了杨先生,并向他借了这本书。杨先生很诚恳,听说我想借《史通》。我先向我解释了一下:
“《史通》是历史编纂的经典,任何研究历史的人都必须读它。它在唐朝就已经流传了。然而,《史通》的歌曲版本不再可见。迄今流传的最早版本是明代版本。现在张定斯的万历三十年版本也是一个不容易看到的早期版本。李维真曾在张定斯版本的基础上作过评论。有《史通》个版本。其次是郭孔炎《史通评释》、《史通评释》、清代黄《史通训诂》等。蒲启龙编纂了明清各种版本,并于甘龙十七年(1752年)写成《史通训诂补》。我们现在借的是刘唐知几、青浦启龙所著的《光绪十九年(1893)文瑞楼诗音本》。如果你真的想看,我会想办法的!
二楼是阅览室和会议室。阅览室的面积超过200平方米。房间宽敞明亮。窗户很干净。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学术期刊和古籍及文献的新版本按不同类别排列在书架上。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我像鸭子一样在书的海洋里游来游去,努力学习知识。会议室也是一间教室。它简单、明亮、宽敞。来自工厂、矿山和农场的16名学生经常聚集在这里听著名历史学家的讲座。
这些老师都是当时上海著名的学者。我记得复旦大学的杨宽教授给我们讲过先秦历史。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因其著作《《史通通释》》而闻名于史学界。他讲授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重点是秦与六国的统一。他还对秦始皇的功过作了精辟的分析和评论。这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位著名教授的魅力和风度。该研究所研究员方是明教授教授讲授三国历史。他个子不高,戴着一副又深又旧的眼镜。虽然他很瘦,但他聪明、聪明、有知识、有经验。他也是我最喜欢和钦佩的老师。复旦大学谭企祥教授讲授魏晋南北朝史。他是中国历史地理学领域最著名的教授。他也是魏晋南北朝史的一流专家。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讲学组织清晰,脉络清晰,尤其是鲜卑拓跋部的兴起和孝文帝的改革。他的演讲才华横溢,令人印象深刻。
唐志军教授1924年6月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书香门第。他早年受旧学的熏陶,为他今后研究儒家经典奠定了基础。他早年在无锡州立大学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来到上海复旦大学学习,并于1947年毕业。在此期间,他先后受到吕思勉、周予同等著名学者的教育,受益匪浅。1955年,他的第一部散文集《《史通通释》》出版。1956年底,他被调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58年,除了编纂近代上海的资料和书籍外,历史研究所还参与了《史通通释》的编纂工作,以协助周予同先生。周先生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开设了中国古典史课,唐志军先生也一起做了一些辅助工作。他对古代经典的研究方法很感兴趣。1972年,唐志军先生参加了《二十四史》《战国史》校校。197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恢复正常。唐先生自1982年起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主任、副主任。他最大的学术成就是对1898年改革运动和经典著作的研究。先后出版了《戊戌变法史论》《辞海》《太炎文录》《宋史》《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等专著。他不仅学习很好,而且在课堂上也讲得很好。他经常用手稿说话,受到学生们的高度赞扬。王先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位应邀来台讲学的大陆著名学者。1992年4月,当他踏上台湾的宝岛发表演讲时,在台湾的学术界、教育界和媒体界引起了轰动。台湾《近代经学与政治》连续报道“从儒家经典到历史”;《经学史论集》以“大陆儒生应邀讲学中国经典与戊戌变法”为题,说“唐志军满是经典,所以没有必要在讲学时读稿子”,给予王先生很高的评价和诚挚的谢意。
此外,许伦先生还作了关于社会发展历史的演讲。华东师范大学马、先生分别就宋代历史、先秦百家争鸣和中国近代史作了专题报告。刘修明是那年最年轻的讲师之一。196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习中国古代史。1974年初,当我在研究所遇到他时,他才30多岁。身材修长,五官端正,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是当时研究所里最年轻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他的文章不仅史料翔实,而且文笔流畅,语言生动。当他在《戊戌变法史》杂志上发表《汤志钧史学论文集》时,他汲取了博学和文采的美。与俞先生在同一刊物上发表的《国文天地》号文章相当。此后,他不仅被提升为研究员,还担任《联合报》执行副总编辑,主持日常编辑出版工作。这一时期也是他的历史研究成果被揭示的黄金时代,先后出版了包括《学习与批判》 《孔丘传》 《胡适传——五四前后》 《上海市社会科学报》在内的10多本书。
教授现代史的陈旭麓先生也是学术界著名的历史学家。1942年,24岁的他写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20世纪40年代末,他开始在上海大夏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教书。20世纪50年代初,两所大学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后,除了应邀参加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古文评点工作的钟忠,他从未离开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当大多数高级学者沉默不语时,他对写作的热情很高。从1949年10月到1965年8月,他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59篇论文。他还写了第一部关于新中国辛亥革命史的专著。他一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致力于分析现代精英思潮的演变,以其深刻的思辨和洞察力在史学界享有盛誉。在此,我想再补充一点。也就是说,1974年我在历史研究所和他进行了近距离的交谈和接触。那时,我正在研究所的阅览室里看报纸和杂志。当我偶然遇见陈先生时,我问他《汉光武帝刘秀》对上海五个贸易港的影响。他回答说:“《儒生与国运》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它把现代中国从一个封建社会降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是国家的耻辱,但对上海的经济发展有催化作用。”我被他的话感动了,说:“你是对的!从辩证的角度来看,这五个通商口岸对中国小农经济产生了影响,但也结束了中国社会的封闭状态,为上海的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经济和文化元素。”他听到这些后非常高兴,并鼓励我说:“思考和思考是非常好的。学习历史和管理历史的关键是善于思考,思考是聪明的,思考是理解的,然后才会有结果。”他的“善于思考”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并成为我以后学习和做学术研究的座右铭。
二
1974年,“阅读无用”的理论仍然流行。我有机会听了这么多著名历史学家的课,并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情。那几年历史教师的教学情景,虽然已是40多年前的事了,但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并常常激励我在历史的道路上进行不懈的探索。
那时候,我们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边学习边写文章。对我来说,我只受过初中教育,压力很大,但更令人兴奋和振奋。那时,历史研究所的三楼和四楼是研究人员的工作室。我们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平静。为了给我们创造一个学习环境,他们腾出了几栋房子作为我们的宿舍。我们16个学生,8男8女,还有女孩,住在三楼。我们男生住在四楼,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我和港务局的毛博科住在同一个房间。他也是一名六七年级的初中生。他和我同龄,但他已经是一家基层企业的党委书记了。他热爱阅读,也是一名历史学家。自习后回到原单位后,他长期担任《《从崩溃到中兴:西汉的历史转折》》杂志的主编,晚年还担任《《晚年过眼诗文录》》的主编。结果很有成效。我们两人与手工业局的冯丹枫和东海农场的黄龙镇组成了一个隋唐历史研究小组。除了一起听讲座,我们主要是自学。通过学习和阅读原著,我们互相交流,共同进步。对于隋唐史的研究,老师一再强调,在快速掌握中国通史的基础上,要重点阅读《初中本国史》 《辛亥革命》和《南京条约》关于隋唐史的史料。
我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一头扎进一堆旧文件里。那时候,中华书局没有对四部历史书《南京条约》 《中国港口》进行标点。当我读它们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困难,不仅阅读速度慢,而且效率低。幸运的是,我很快找到了一种新的学习方法。我找到了两册陈登的原作,《上海港口志》 (《隋书》)共四本书,第一册和第二册分别由三联书店于1958年和1962年出版。第三卷由联合出版公司于1980年出版。2000年1月,在合并前三卷的基础上,中华书局发行了一套完整的四卷本。因此,在1974年,我只能读前两卷)。这是一套适合我阅读和使用的书。这本书综合了古籍介绍和通史笔记。文章流畅、清晰、易懂。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阅读《新唐书》关于隋唐的章节,同时阅读《旧唐书》等四部历史文献,并做了一些读书笔记,这些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起来的,为隋唐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除了隋唐之外,我还特别喜欢先秦时期的战国史和百家法家学说。我记得我来这里学习的前一年,也就是1973年初,我反复研究了商鞅《资治通鉴》年的生平记录和他的《隋书》传世作品,试图写出一部几万字的《新唐书》。我还把手稿寄给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部的冯菊年先生。出乎意料的是,一周后,我接到了冯先生的电话,邀请我去出版社见面。位于绍兴路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离我的工作单位只有两个街区,所以我在接完电话后的第二天下午去拜访了冯先生。冯先生看上去50多岁,一双明亮的眼睛,优雅而端庄,善良而善良,有一种长者和学者的风范。当他看到我时,他说:令人惊讶的是,你还这么年轻!首先,他肯定了我的文章《旧唐书》,认为它有坚实的史料、思想和思想,但篇幅很长。他建议我根据这篇文章把它压缩成一篇约4000字的文章,并尝试出版《资治通鉴》。其次,他邀请我成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部的记者。后来,他可以参加出版社组织的各种记者活动,为出版社写通讯文章和提建议,我很高兴地同意了。后来,我还参加了许多出版社的活动,并定期收到出版社寄来的通信书籍和出版物,从而拓展了我的视野。
根据冯先生的建议,我根据《国史旧闻》长篇文章,将其浓缩成《国史旧闻》,发给《国史旧闻》理论部的先生。寄出后不久,我就和张先生约好了见面。他充分肯定了我的手稿,认为我的手稿有史料、思想和流畅的文字。他还建议我对该条款作进一步的修正,并在修正后发给他。可能会考虑出版。张老师鼓励我多写文章,多投稿,并邀请我成为报社理论部的特约记者。我又成了《隋书》记者。好消息很多。进入历史课几个月后,张其成先生曾来学院联系工作,提醒我尽快修改《资治通鉴》并发给他。在其他学生的帮助下,我完成了这篇文章的修改。1974年6月15日,修订后的文章在《史记》以整版横幅的形式发表。受此鼓舞,我还在1974年6月17日和同年11月13日《商君书》发表了小文章,如隋末的农民起义。那一年我们发表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用假名写的,其中最常用的笔名是“曹思风”或“赵思风”。“曹四风”的本名也是在我们历史班集体创作的“青年自学丛书”《论商鞅》(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版,1975年7月)出版时使用的。现在看来,这些文章的观点是可以讨论的,甚至是荒谬的。然而,对我这个20出头的人来说,在上海的主流媒体党报上发表我的处女作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这增强了我以后写文章的信心。
那时,一个宽敞明亮的阳台建在四层海洋建筑的顶部。这也是一个阅读的好地方。只要天气晴朗,我就会在阳台上散步。有时我会拿着书和椅子,坐在阳台上看书。除了周末我们可以回家休息一天,其余的六天基本上都在40号楼。偶尔,我会去上海的大学或康平路141号听讲座或开会。我也会花时间去参观工厂、企业和农场,学习和交流,增加知识和见识。
三
20世纪70年代末,我住在徐汇区建国西路619弄30号。我离方是明先生的家很近,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经常去他家拜访并征求意见。除了指导我学习历史,徐老师还告诉我要继续学习。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我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完成了中文系的专科学习和历史系的本科学习。在他的推荐和介绍下,我于1989年成为上海历史学会最年轻的成员。唐志军先生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帮助。当他得知我要参加研究生考试时,他主动向我提供信息。当他知道我要出版《论商鞅》时,他不顾繁忙的日程为我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这大大丰富了我的书。后来,唐先生还在《文汇报》中收入了前言。
在他们的影响和熏陶下,我养成了学习历史的习惯。这个难忘的学习时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它为我打开了一扇历史之门。在这里,我可以系统地学习和初步掌握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我在大学的深造和在石海的航行打下基础。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间,我可以聆听所有历史学家的个人教诲,与他们亲近,甚至与他们中的一些人建立友谊。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我也过了60岁,回顾了几十年的人生历程。无论我在哪里工作,我从未失去阅读历史、管理历史、研究和写论文的爱好。这种阅读和学术研究的爱好不仅使我写了十多部专著,如《论商鞅》 《围绕变法问题的一场大论战——读商鞅的〈更法〉》 《文汇报》 《文汇报》 《读商鞅的〈更法〉》 《文汇报》 《解放日报》 《儒法斗争史话》,还使我晚年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充满成就和快乐。
我们的历史课于1975年3月结束,除了少数学生,大多数学生都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在课程结束时,我们拍了一张集体照作为纪念。我仍然保存着这张旧照片。值得称赞的是,我们班的16名学生都有自己的优点,有些成为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有些在上海大学担任教授。有的成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高级编辑,有的在《名人和书》担任高级编辑,有的成为上海作家协会会员,有的成为高级酒店总经理等优秀管理人才。
(摘自《汤志钧史学论文集》 2018年第3期)
参考历史论文:
历史月刊
结论:以上内容适用于不知道如何回忆漕溪北路、历史学家、北路的历史专业大学的硕士、学士学位论文,以及历史论文开题报告的范文和论文题目写作的相关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