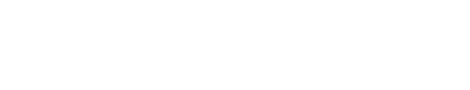电影铁皮鼓,铁皮鼓无删减观看
我一直在和奥斯卡以及他的亲戚朋友争论。如果有人记录下我们的谈话,并把它编入小说《铁皮鼓》的附录中,成品将会多出200页。自从我在《铁皮鼓》开始写作,这个小屋也成为了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在那里我一直从事断断续续的雕塑创作。房间里的湿度可能有助于奥斯卡马特拉的幽默感。因为安娜是瑞士,公民,所以每年夏天我都会在提契诺州,瑞士,呆几周,在户外写作。
我在一封信中写道:“忏悔:我是一家疗养院的居民……”随着小说第一句的出现,障碍被清除,成千上万的单词涌出,记忆和幻想展开翅膀,正式的游戏和详细的描述获得了自由的空间,一章接一章的内容变得自然。当岩石阻碍叙事之河的流动时,我会跳过它。关于当地市场的故事涌入我的脑海。罐头食品上下跳动,释放出它的异味。我构想了一个繁荣的家庭。我一直在和奥斯卡以及他的亲戚朋友争论。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描述电车和它们的路线,如何安排同时发生的事件,如何摆脱时间顺序的荒谬束缚,是否让奥斯卡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的形式来描述它,是否满足他做爱和生孩子的要求,以及如何赋予他现实的错误和想象的罪恶。
我试图给古怪的奥斯夫配备一个邪恶的小妹妹,但在他的抗议下,我的尝试失败了。这个被封杀的小妹妹坚持她的文学生存权,后来她出现在我的其他作品中。
现在我想回答一个大家经常提到的流行问题:我不为读者写作,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任何读者。第一,我为自己写作,第二,我为安娜,写作,第三,我为偶然来到我寒舍听我的书章节的朋友和熟人写作。我用我的想象力召集了一群读者,我为这群虚构的读者写作。活人和死人围着我的打字机。其中有我的朋友格尔德马赫,他忽略了细节,还有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一位戴着厚厚眼镜的文学导师(注:阿德布林(1878-1957)。德国小说家,小说《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 (1929)、《王龙三跳》 (1915)和《华伦斯坦》 (1920)等的作者。),我的岳母,她熟悉文学,相信真、善、美,风尘仆仆、四处逃窜的拉伯雷,我的前德文老师(我认为他古怪的脾气比当今教育体系中的干果供应更有效),还有我已故的母亲。我用各种文件来处理她的反对意见和修正案,但她只相信我有所保留。
当我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仍然记得我和这群挑剔的读者进行了一次长谈。如果有人记录下我们的谈话,并把它编入小说《铁皮鼓》的附录中,成品将会多出200页。
也许意大利大街111号的大火吞噬了这个附录,也许我们的谈话纯粹是虚构的,因为我对写作过程的记忆非常模糊,而我对我的工作室的记忆却是生动的。那是一层潮湿的小屋。自从我在《铁皮鼓》开始写作,这个小屋也成为了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在那里我一直从事断断续续的雕塑创作。同时,这个工作室也是我们楼上两居室小房子的供暖锅炉房。我既是作家又是司炉。每当我想不出主意时,我都会走出工作室,从面向街道的小屋里带回来两桶可乐。我的工作室散发着地窖细菌的气味,充满了气体,让人感觉亲切。水淋淋的墙壁让我的想象像一条大河,绵延数千英里。房间里的湿度可能有助于奥斯卡马特拉的幽默感。
因为安娜是瑞士,公民,所以每年夏天我都会在提契诺州, 瑞士,呆几周,在户外写作。我坐在铺满葡萄叶的凉亭里的石桌旁,望着波光粼粼的南方风光,描述着被冻得大汗淋漓的波罗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