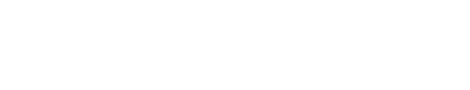美国城市的死与生,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街道眼的概念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很少有墓地。全国平均水平约为14万元人民币,墓地不能买,只能租。更不用说大城市,在大城市,中国,不仅看不到墓地,甚至没有公开悼念的余地。死亡为活着的人提供了便利,这并不不幸。除了远郊的八宝山,北京,唯一与生死相关的建筑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政治化的死亡属于政治,不属于人。死亡已经成为修辞的意义。我认为不以延长生命为目标的生活可能有些不同。
不久前美剧《纸牌屋》,英雄的妻子有每天早上跑步的习惯。一天,她很自然地跑进了社区的墓地。
这一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出国旅游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社区里经常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墓地群。事实上,他们不是很严肃。许多坟墓杂草丛生,但这种感觉并不可怕和荒凉,而是自然的。每当我经过一个墓地,我总是为了一个非常自私的目的进去转身:在死者中,我可以非常肯定地感觉到我还活着。
我看过一个建筑设计。在德国,西部的迪伦镇,该镇东部的墓地已经作为一个公共公园开放。公园的墓地里建了一个咖啡馆,人们可以在那里交流或回忆。咖啡馆被反光玻璃包围着。墓地的风景投射在玻璃上。活人被死人包围着。两者融为一体,只有新鲜和温柔的感觉。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很少有墓地。
有人可能会说,这属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是由于西方人对基督教的信仰。然而,在东方的日本,东京随处可见一个没有围墙的小墓地。在日本的墓地上立着一个方形的圆柱形石碑,石碑后面立着一个象征佛塔的长木板。我读过李长声,的一篇文章,他是一位去日,旅行的作家,他介绍说日本的葬礼是由他所属的寺庙组织的。丧葬费非常昂贵。全国平均水平约为14万元人民币,墓地不能买,只能租。
我想起了中国的墓地。前年年底,我父亲打电话来说他的家乡被拆除了,我祖父母的祖坟被移走以补偿2000英镑块钱英镑),这样我就可以在网上发帖反映这件事。我父亲一直害怕我惹麻烦,但这次我劝他不要再惹麻烦了。活着的人很难抗拒拆迁,更不用说死人了。
这是在一个偏远的小镇上,没有足够的空间建墓地。更不用说大城市,在大城市, 中国,不仅看不到墓地,甚至没有公开悼念的余地。
我第一次有公众悼念的概念是在去年我去爱丁堡的一个公园的时候。我每隔几步就看到一条长凳。长凳上刻有我心爱的妻子/已故父亲的记忆和其他字-like图像。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哀悼不一定是痛苦的。死亡为活着的人提供了便利,这并不不幸。
除了远郊的八宝山,北京,唯一与生死相关的建筑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然而,除了它想象中的威严之外,它没有给人任何其他的感觉。政治化的死亡属于政治,不属于人。
城市里的人们离死亡越来越远。死亡已经成为修辞的意义。在日益明亮和现代化的城市日,死亡并没有体现出来,除了冬天晚上偶尔在街上走一走。
古人把美丽的春秋日作为他们的挽联,在山川中发出清脆的声音。天地之间无忧无虑的山川、清澈的茂林,和美丽的瞬间被生者和死者分享。今天的人们在死后焚烧纸质豪华房屋和汽车以及低得离谱的大面额冥币,与其说是为了死者,还不如说是为了欺骗自己:死者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比特里斯坦更加遥远和未知。
人们是否觉得死亡可怕取决于他们离死亡有多近。作家三毛曾经写道,她逃学去墓地学习。因为墓地很安静,她写道:与死者作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事情。他们都是非常温和的人。你越逃避死亡,就越害怕死亡。
一位住在北京的作家曾经告诉我们,在北京,他最害怕去八宝山的方向。回到我的家乡,我最害怕看到老人和病人瘫在村庄入口处的阳光下。他去八宝山为已故的老作家送行。他回来后,连续三晚失眠。他后悔去了一个充满了字,节日祭品、字和黑白花的地方。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祖父去世了,我回到了我的家乡参加他的葬礼。出于某种原因,我不能哭。然后我父亲掀开了覆盖在爷爷身上的白布。我看着他苍白的黄瘦的脸,立刻哭了。眼泪不是来自悲伤,而是来自恐惧。死亡对我来说很奇怪,很可怕。然而,死亡真的很奇怪吗?
它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慢慢侵蚀着生命的力量,生命的虚弱、干燥和消失不断发生。人生的无常和无常总是一样的。然而,我们愿意思考光明的生活,逃避死亡的想法。我们讨厌思考从死亡中获得对我们的生活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东西,并把它与我们压抑的潜意识联系起来。
我们如何看待死亡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生命。阅读日本中世纪武士道的原始代码《叶隐》,有四个字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死而复生。我认为不以延长生命为目标的生活可能有些不同。我将牢记三岛由纪夫对这一点的解释:如果我们太固执而不愿在渴望生存的时候生活,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可能会偏离我们生活的伟大之美。
第二天: 侯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