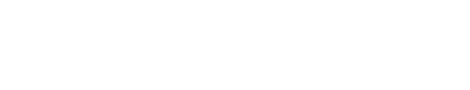怀念萧珊原文以及赏析(怀念萧珊)
今天是萧珊逝世六周年。六年前,它仍然出现在我的眼前。那天,当我从火葬场回家时,一切都乱七八糟。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平静下来。我独自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文章来纪念她。五十年前,我有这样一个习惯,当我有感觉,无处倾诉时,我经常求助于纸和笔。我痛苦地想,如果牛棚关了几年,它真的变成了牛头上的一块大石头,想得像被冻住了一样。我只是放下笔,什么也没写。我们哭着向萧珊的遗体告别。她用尽一切办法,直到去世前三周。
今天是萧珊逝世六周年。六年前,它仍然出现在我的眼前。那天,当我从火葬场回家时,一切都乱七八糟。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平静下来。我独自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文章来纪念她。五十年前,我有这样一个习惯,当我有感觉,无处倾诉时,我经常求助于纸和笔。但在1972年8月的那些日子里,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看着摊在我面前的报纸,但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痛苦地想,如果牛棚关了几年,它真的变成了牛头上的一块大石头,想得像被冻住了一样。我只是放下笔,什么也没写。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和他们的书呆子们确实把我搞得一团糟,但我还是活了下来,我活得很健康,头脑也不糊涂。有时我可以写一两篇文章。最近,我经常去墓地参加老朋友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了许多事情。我也玩过悲欢离合,但我的思绪从满是人的大厅转到了只有十或三十个人的大厅。我们哭着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得觉新在家里说过的话。看来珏已经死了,而且还是一个不祥的幽灵。当我在47年前写下这句话时,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我没有流泪,但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挠我的心脏。我站在尸体旁边,看着苍白的脸和两片吞噬了成千上万个单词的嘴唇。我咬紧牙关,在心里呼唤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认为这太不公平了!她犯了什么罪?她被关在牛棚里,挂上幽灵般的小卡片,横扫过马路。原因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病了,不能得到治疗,因为她是我的妻子。她用尽一切办法,直到去世前三周。她通过打开后门住进了医院。但是癌细胞扩散了,肠癌变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想活下去,她愿意改革她的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不能说是一厢情愿。如果她不是黑老k的臭妻子,她可能还活着。总之,我连累了她,伤害了她。
在我靠边停车的那些年里,我遭受了同样的精神折磨。但我没有被打,但她得到了北京红卫兵的铜头皮带,几天后她左眼上留下的黑眼圈消失了。她被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到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会把我带走,所以她溜出了大门,去对面的警察局要求警察同志干预。只有一个人值班。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很多安慰和鼓励。四害猖獗的时候,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被视为罪人和贱民。有时我直到晚上9点或10点才回家。我穿过门,看到了她的脸,我脑海中的乌云消失了。我可以向她倾诉我的不满和抱怨。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和我可以。她用同样的声音回答说生活是艰难的!然而,她立即补充说,她应该坚持下去,否则坚持就是胜利。我说生活是悲伤的,因为在那段时间里,我每天都在牛棚里工作,学习,写账目,检查和写思想报告。任何人都可以骂我,教训我,指导我。从外地来作家协会分会的人可以随意叫我出来给公众看,举报我的罪行。通勤时间没有限制。这是由负责牛棚的监督小组随意决定的。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拿走他们喜欢的任何东西。这时,群众批评和电视批评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却越来越近了。
她说生活是悲伤的,因为她两次被拉到办公室,停下来工作,后来经常参加陪护打架。淮海中路的批评栏上贴了一张批评我犯罪的大字海报,我家人的名字也被写了出来供公众展示。不用说,一个臭女人的名字占据了突出的位置。这些话像虫子一样咬着她的心。她让上海戏剧学院傲慢的学生突然袭击,当他们开到作协支部时,他们还在我家门口贴了一张。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讽,蚕吃了她的身心。我可以看出她的健康正在逐渐受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就像一壶开水。她怎么能掩饰呢?你怎么能让它平静下来!她不断安慰我,表达对我的信任,并为我感到委屈。然而,当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时,我的压力一天比一天大,她非常担心。有时她去上班或和我一起工作,走近巨鹿路口,走近作家协会分会,或走近湖南路口,走近我们家,她总是抬不起头来。我理解她,同情她。我也很担心她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有一天,当我们下班时,我们没有遭受任何困难。当她回到家时,她很开心,去厨房做饭。我看了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看到当时作协支部的两位领导人,即工人和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暴露了巴金的反革命面目。这是一个打击!我读了两三行,很快就把报纸藏了起来。我担心她会看到。她带着熟食走了出来,脸上带着微笑。她吃饭时有说有笑。她想在晚饭后看报纸,我试图把她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但这没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突然消失了。那天晚上她再也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