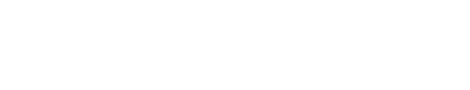看得见的正义电子书(看得见的正义)
几天前,在去长春的火车上,我偶然发现了一条新闻。是新华网电《中国籍老人被勒令离境惊动芬兰部长》。内容大概是说,一位中国籍的退休工人为了留下来照顾他的孙子,与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并想向芬兰移民局申请一份基于雇佣关系的居留证,以代替即将到期的旅游签证。芬兰内政部长关注此事,并要求芬兰移民局解释此事。
因此,我想知道,虽然作为内政部长的巴伊韦莱森宁吉有责任协调和联系该国移民局的工作,但他不是该国法律和立法的直接领导人。他怎能根据自己的经验要求移民局解释这件事,“祖父母通常有能力照顾孩子,这不需要培训”,并问芬兰是否需要根据新的社会需要修改移民法?我认为这在被瑞典统治了近六个世纪的欧盟国家中是不可思议的,这些国家“强调程序而忽视实体”。我想,几个星期后,芬兰移民局答复说,它肯定不会改变初衷,坚持它所作的决定。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可见的方式实现”。用法律来充分保护公民权利和实现实体正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实现程序正义。丹宁勋爵很久以前就告诉了我们这个事实。程序正义是“法治”不同于任意甚至任性的“人治”的重要标志之一。说它是风向标不算过分。
起初,直到几天前,我还不知道所谓的法律是由实体法和程序法组成的。而所谓的程序法,也就是几个民事行政诉讼。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大错误。本来,非程序法,包括行政程序法、立法程序法、选举规则和程序规则,都是程序法的一部分。程序法和实体法这一庞大家族的合作、共同运作和综合运用构成了日常的审判活动。
为了保证审判结果的公正性,司法工作不仅要重视实体性判决,还要重视程序性判决。通过实施这些程序,每个人都必须有机会参与决策或了解决策过程,然后才能做出与其权益相关或不相关的决定。对于当时利益对立的人,他们也应该保持中立和客观,以平等的参与机会和平等的参与能力参与其中,使决策者能够以审慎的态度谨慎地做出限制甚至无情剥夺他人权益的决策。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认为在中国的司法审判中有一种“渴望成功”的错觉。事实并非如此。一个普通的基层法院只需要几个小时的审判,就可以宣布被告有罪或无罪。对于影响大、案情复杂、破案困难的案件,法院会加班加点,“开夜车”。不,即使在陈希同、陈良宇甚至薄谷开来的案件中,法院也没有超过一天的时间进行审判活动。我认为,原因是中国仍然是一个“重实体、轻程序”的国家。
虽然“重实体轻程序”可以简化司法活动,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这让我想起了1957年夏天的中国和60年代中期的中国。我不得不说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百年的悲哀。没有人能数清有多少审判流于形式,也没有人知道有多少截止审判是以个人意愿为标准进行的。不要说那些“不要怕死不避,不要破坏节日而生存”的文人受到迫害,就连堂堂的共和国总统也难免在死后多年才平反冤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著名的“纽伦堡审判”。尽管这些战犯因他们的罪行而臭名昭著,但裁决者并没有依靠“木锤”,而是依靠堆积如山的铁证来对他们进行审判。充分听取每个受审人的辩护意见,让“听取和吸收双方的辩护意见”落到实处。我不得不说,我不得不佩服那些司法工作者的态度。我想这就像中国的一句老话,“你听什么,你就听什么,你就听什么,但你就听什么。”。多余的程序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收获是对他人、后代甚至历史负责的。利益受到他人审判的直接冲击和关联的人应当发表意见,提出自己的证据和理由来反驳对方,从而对裁决者施加压力,对裁决结论产生积极影响。让程序正义避免审判过程中的权力滥用和失职。
“愿世界上没有不公正”。我很幸运地在福州中级人民法院的走廊墙上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是的,如果你想判断无罪与否,证据的存在无疑是判断的重要依据。法定证据制度的存在标志着法定证据的判断原则逐渐浮出水面,并引领和推动了证据规则这一基本概念的发展。因此,司法工作者或国家行政人员,无论是依靠所谓的经验和常识,还是根据一些所谓的“理性推论”,都不能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确认任何事实。“祖父母通常有能力照顾孩子,这不需要训练”和“是否编一份虚构的工作”,这并不是事实。也许在现实生活中,事实是,正如普通人认为的那样,移民局也应该为他们的定居签署一份许可证。然而,由于不同程序的不确定性,它也可能是一个虚假的事实,甚至只是一个假设的事实。但那又怎样!俗话说,“没有规则,就没有方圆”。我认为,芬兰移民局的做法似乎有些僵硬、不灵活,甚至不人道。众所周知,它可以更好地保护更广泛人群的利益,平等对待他们,不考虑情感因素。
"不能被有效证实的事实等于不存在!"世界上不乏远见卓识,罗马法谚语似乎击中了要害。“没有照顾孩子的工作经验”,“在回答警察的询问时,我分不清工作时间”。如果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不这么认为。我相信,在本质上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工具而存在的法律,在今天的中国会更好地实现其独特的价值,即“重实体,轻程序”,“重国家,轻两个创新”,让正义为世人所见!